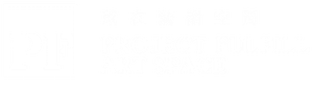Stone
Chan Shih-Tai Solo Exhibition
石子-詹士泰個展
Artist talk record 座談記實
與談人:許遠達 × 賴志盛 × 詹士泰
與談人:許遠達 × 賴志盛 × 詹士泰
詹士泰,許遠達
許遠達:歡迎大家在假日前來參與詹士泰石子在就在藝術的展出,我們今天邀請到知名藝術家賴志盛,還有我許遠達來跟大家談一談詹士泰的作品,我們兩個很久以前就認識詹士泰了,談作品也經常在談,待會進行的方式請詹士泰談一談之前的創作態度跟這一次展出的創作態度從《我不是車床》這種非常硬蕊的姿態、硬來的感覺,到目前《石子》很放鬆的、很自然的一種狀態,光展名就讓人家覺得很像有在放鬆的感覺,那就請你談一談你的創作轉變。
詹士泰:這個展覽就我個人在創作上來講,算是近三年來比較有一個明顯的調整,主要是在我取得這個材料的當下,我跟這個材料互相影響、互相介入。我會比較著重在這部分是因為我過往把材料當作是被我利用的一個角色而已,那這三年來的時間,我覺得是我對於石材這個材料,會更注重我跟它之間的關係。當我在工作前,當我在跟這材料接觸的時候不單單只是在自己的創作、或自己的想法、或所謂的一種能量,就是全部的灌輸在這個材料上然後要做一個這個材料很大的一個翻轉,反而現在會覺得,試著讓我自己面對這個材料的時候,可以有種盡可能是輕鬆的態度,能夠跟它有一個比較平等的位階去看我的工作。
如果再回憶起來剛剛許遠達講的,在劉和讓的工作室(汐止)辦的個展,當時的作品會有那樣一個名字的產生,是當時在創作上的想法會著重在點線面的一種比較全然的處理,我希望在作品上面透過點線面的部分幾乎全然的包裹,把我自己對當下的一種情緒跟環境對我的影響,做一個比較冷調的處理,我也刻意去把人的一種溫度、生活上面不確定性的東西盡量排除掉,所以當時距今大概2012-2013左右的時間,差不多十年前,會比較獨自,類似有點孤僻。在工作上面的心態來講,會覺得人的部分、生活上面不確定性的、不擅長的東西會盡量的把他排除在點線面的一種幾何東西之外這樣子。之後慢慢慢慢的也經歷了一段時間,到了大概「絕對空間」2015、2016,那個時候,還是處在一個盡量保持類似的質地,後來有再做一點反思,在處理得極致的時候,是不是自己還是缺乏跟這個材料有更細部的一種交流、或者是更深的一種體認。
那所以在「外子」空間2020年尾十一月的展覽,那時候我大概有嘗試幾件作品,試著開始在工作室的周遭,讓自己去探索一些工作環境的角落,然後慢慢地去發掘一些過往會被我忽略的材料或一些物件再漫漫的去觀看,過往取得的材料會做一番清洗之後,再將一些青苔或是不規則面,會做一些修整之後才會變成我會去用的一些材料。後來在2020年時,我開始試著讓過往會在意或閃避的東西,讓自己直接去面對。所以我把取得材料當下的狀態,不見得是裸石,可能是過去工廠或別人廢棄的東西,去做一個審視,覺得這樣的材料它已經加諸了很多時間性在裡面,不管是青苔、油漬、或是灰塵,它們在上面的痕跡,對我來講都是一種可能性的生活軌跡,那我也沒有必要再把石材一定要恢復到一個乾淨的狀態,或是外型要是一個所謂完整的狀態。所以我透過這樣子的實驗慢慢把自己跟當下環境的互動關係銜接起來,也不再讓自己的工作的慣性總是把很多事情的條件排除在外,我覺得這樣的嘗試也讓自己在工作過程當中心態上也不再是走在一種稜線上面,總是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跟我比較沒有相干的,我自己的創作上來講,會跟著環境的,可能是聲音、可能是一種溫度,會漸漸地在我工作中慢慢的去累積,慢慢的去液露出來,所以這次的作品,大概可以感覺到我保留了這個材料原本的狀態的比例會開始有一些量的增加。
許遠達:從一開始我們認識詹士泰的這種,非常用極端的個人自我意識去包裹的媒材,那這個媒材就像他剛剛講的,只是一個媒介,它似乎是感覺,其實是木頭、是石頭它的差異性並不大,但是在近來的展覽就可以發現到他在跟石材對話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強烈,這個其實在某個時機點也接上你在幫賴志盛處理一些作品的那時候,也蠻有趣的,作為一個貼身的朋友,也作為一個專業的藝術家,那我們請賴志盛也來分享一下他怎麼去看詹士泰的作品。
詹士泰:這個展覽就我個人在創作上來講,算是近三年來比較有一個明顯的調整,主要是在我取得這個材料的當下,我跟這個材料互相影響、互相介入。我會比較著重在這部分是因為我過往把材料當作是被我利用的一個角色而已,那這三年來的時間,我覺得是我對於石材這個材料,會更注重我跟它之間的關係。當我在工作前,當我在跟這材料接觸的時候不單單只是在自己的創作、或自己的想法、或所謂的一種能量,就是全部的灌輸在這個材料上然後要做一個這個材料很大的一個翻轉,反而現在會覺得,試著讓我自己面對這個材料的時候,可以有種盡可能是輕鬆的態度,能夠跟它有一個比較平等的位階去看我的工作。
如果再回憶起來剛剛許遠達講的,在劉和讓的工作室(汐止)辦的個展,當時的作品會有那樣一個名字的產生,是當時在創作上的想法會著重在點線面的一種比較全然的處理,我希望在作品上面透過點線面的部分幾乎全然的包裹,把我自己對當下的一種情緒跟環境對我的影響,做一個比較冷調的處理,我也刻意去把人的一種溫度、生活上面不確定性的東西盡量排除掉,所以當時距今大概2012-2013左右的時間,差不多十年前,會比較獨自,類似有點孤僻。在工作上面的心態來講,會覺得人的部分、生活上面不確定性的、不擅長的東西會盡量的把他排除在點線面的一種幾何東西之外這樣子。之後慢慢慢慢的也經歷了一段時間,到了大概「絕對空間」2015、2016,那個時候,還是處在一個盡量保持類似的質地,後來有再做一點反思,在處理得極致的時候,是不是自己還是缺乏跟這個材料有更細部的一種交流、或者是更深的一種體認。
那所以在「外子」空間2020年尾十一月的展覽,那時候我大概有嘗試幾件作品,試著開始在工作室的周遭,讓自己去探索一些工作環境的角落,然後慢慢地去發掘一些過往會被我忽略的材料或一些物件再漫漫的去觀看,過往取得的材料會做一番清洗之後,再將一些青苔或是不規則面,會做一些修整之後才會變成我會去用的一些材料。後來在2020年時,我開始試著讓過往會在意或閃避的東西,讓自己直接去面對。所以我把取得材料當下的狀態,不見得是裸石,可能是過去工廠或別人廢棄的東西,去做一個審視,覺得這樣的材料它已經加諸了很多時間性在裡面,不管是青苔、油漬、或是灰塵,它們在上面的痕跡,對我來講都是一種可能性的生活軌跡,那我也沒有必要再把石材一定要恢復到一個乾淨的狀態,或是外型要是一個所謂完整的狀態。所以我透過這樣子的實驗慢慢把自己跟當下環境的互動關係銜接起來,也不再讓自己的工作的慣性總是把很多事情的條件排除在外,我覺得這樣的嘗試也讓自己在工作過程當中心態上也不再是走在一種稜線上面,總是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跟我比較沒有相干的,我自己的創作上來講,會跟著環境的,可能是聲音、可能是一種溫度,會漸漸地在我工作中慢慢的去累積,慢慢的去液露出來,所以這次的作品,大概可以感覺到我保留了這個材料原本的狀態的比例會開始有一些量的增加。
許遠達:從一開始我們認識詹士泰的這種,非常用極端的個人自我意識去包裹的媒材,那這個媒材就像他剛剛講的,只是一個媒介,它似乎是感覺,其實是木頭、是石頭它的差異性並不大,但是在近來的展覽就可以發現到他在跟石材對話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強烈,這個其實在某個時機點也接上你在幫賴志盛處理一些作品的那時候,也蠻有趣的,作為一個貼身的朋友,也作為一個專業的藝術家,那我們請賴志盛也來分享一下他怎麼去看詹士泰的作品。
「石子」詹士泰個展現場,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tone' Chan Shih-Ta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2)
賴志盛:大家好,那剛剛來的路上,就想了幾個點,因為我上次在「外子」空間詹士泰展覽的時候也看了蠻多他的最近的發展,有歸納幾個點,第一個是,我覺得當代藝術裡面現在花很多時間去面對一個物件,很長時間的投入在一個空間的機會很少,大部分就是用腦袋跟很快速的時間,去處理他眼前的這些材料這些想法,那一直變換一直變換;但是像打石頭這個是時間要長的、而且要穩定的、對這個材料要細緻地處理的方式,我覺得這點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就在當代來看。所我看到詹士泰的作品,包括很多痕跡你可以感覺它像是一些生活裡頭日常的物件,比如說像蛋糕,有的像一個槽或是我們所看到一個大小痕跡的形狀,所以他在這裡面的明暗、光影,或者是本身材料所透露出來的感覺,或多或少從他自己的點線面的工作,轉換到比較像生活感、日常的經驗裡頭,一起產生在這個作品裡面,這是我看到覺得蠻會心的地方。
第二個是他作品裡面的痕跡我覺得很有趣,他留下來這些舊的痕跡不是這石頭真正的表面,只是它石材的表面,所以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有點無聊沒洗乾淨或是髒髒的,或是其實覺得它是青苔好像放在一個地方很久了,這個痕跡,表面上你看起來會沒什麼,我發現他花很多時間把它雕刻出來的地方,它反而是新的,那他留下這表面的痕跡就產生了一個反差,這反差裡頭透過一個比較像時間、或是灰塵、髒污,把它保留像是一個繪畫表面,或材質的表面,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反的動作,他保留下來的反而是有痕跡的,那他自己的痕跡是新的痕跡。
另外一點就是他把「草圖」,留在作品裡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鉛筆線,箱子上也是,到處都是他工作的一個書寫或是一個描繪的痕跡,他一樣把這東西留在上面,保留一種接近它,有時候是超過一點點,有時候是沒有碰到它的鉛筆的痕跡,我覺得這也是在一個語彙裡頭放鬆的地方,不一定是要把「完整」給你看,但他把他接近它的方式給你看,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第三個是你看到他作品常有很多薄薄的石材,讓它盡可能去單薄化它,但是單薄化的過程裡頭,看到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是跟光影有很大關係,他創造的其實是一個陰影的空間,有些是整體的重量它只是挖了一個地方,像是那件三角形像蛋糕的底盤,他在下面做的是一個不是中心點的突出,所以它就會創造一個陰影的空間,這個我覺得也是他把作品本身的量體跟材料的某種「鈍的感覺」轉換成一個「輕盈」的狀態,那也把周圍的這個光,跟他的作品產生一個新的對比,或是一個明暗的空間。我覺得他現在做作品,可能也是因為年紀,他對這個材料的體認,真正在掌握這個材料、掌握這個作品的一個方式,事實上不是抓緊它的,它鬆跟緊的時候都是很好的掌握,一般我們認為「掌握」其實就像把一個作品做得完成度,或者是它應該變得是我們覺得完美的狀態,從一個藝術家本身他自己造成,到現在是可以跟石材的互動、這種掌握住但他不是緊抓著它的狀態,我覺得這很好。
第二個是他作品裡面的痕跡我覺得很有趣,他留下來這些舊的痕跡不是這石頭真正的表面,只是它石材的表面,所以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有點無聊沒洗乾淨或是髒髒的,或是其實覺得它是青苔好像放在一個地方很久了,這個痕跡,表面上你看起來會沒什麼,我發現他花很多時間把它雕刻出來的地方,它反而是新的,那他留下這表面的痕跡就產生了一個反差,這反差裡頭透過一個比較像時間、或是灰塵、髒污,把它保留像是一個繪畫表面,或材質的表面,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反的動作,他保留下來的反而是有痕跡的,那他自己的痕跡是新的痕跡。
另外一點就是他把「草圖」,留在作品裡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鉛筆線,箱子上也是,到處都是他工作的一個書寫或是一個描繪的痕跡,他一樣把這東西留在上面,保留一種接近它,有時候是超過一點點,有時候是沒有碰到它的鉛筆的痕跡,我覺得這也是在一個語彙裡頭放鬆的地方,不一定是要把「完整」給你看,但他把他接近它的方式給你看,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第三個是你看到他作品常有很多薄薄的石材,讓它盡可能去單薄化它,但是單薄化的過程裡頭,看到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是跟光影有很大關係,他創造的其實是一個陰影的空間,有些是整體的重量它只是挖了一個地方,像是那件三角形像蛋糕的底盤,他在下面做的是一個不是中心點的突出,所以它就會創造一個陰影的空間,這個我覺得也是他把作品本身的量體跟材料的某種「鈍的感覺」轉換成一個「輕盈」的狀態,那也把周圍的這個光,跟他的作品產生一個新的對比,或是一個明暗的空間。我覺得他現在做作品,可能也是因為年紀,他對這個材料的體認,真正在掌握這個材料、掌握這個作品的一個方式,事實上不是抓緊它的,它鬆跟緊的時候都是很好的掌握,一般我們認為「掌握」其實就像把一個作品做得完成度,或者是它應該變得是我們覺得完美的狀態,從一個藝術家本身他自己造成,到現在是可以跟石材的互動、這種掌握住但他不是緊抓著它的狀態,我覺得這很好。
左:詹士泰,許遠達,賴志盛
右:詹士泰 Chan Shih-Tai, Untitled 無題, 2017, marble 大理石, 37×37×13cm
右:詹士泰 Chan Shih-Tai, Untitled 無題, 2017, marble 大理石, 37×37×13cm
許遠達:那作為主持人的我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詹士泰近來作品的感覺,如果我們從一種過程中去看,之前的作品比較造型的部分、比較忽略媒材的部分有一點是在石頭這個媒材上面的自我意識的建構,自我意識的建構就是說-我不管它的環境或是這顆石頭長怎樣,我想建構什麼樣的造型我就把它推到極致,這個極致的過程我覺得他有一種台灣創作者比較少的,尤其是在石雕領域或雕塑領域比較少的比較絕對理性的部分,我又經常開他玩笑說,它看來像是絕對理性的東西,其實是最浪漫的,因為大家如果知道石材,尤其作品如果不大,它的一些夾角的處理跟一些夾縫的處理其實是最難的,那這些最難的部分你必須要動用很多的技術的控制,但是你要動用更多這種浪漫的想像,就是說:我一定要把它做出來。這就是我們講他是很極端的自我意識建構,那近來的作品我就覺得他有一種接受,從一種極端的、純粹的、內在的自我建構到能更接受的一個過程,包括了有一點點放開的地方會讓你感覺到好像有一點鬆掉或是被破壞那個直線的變化,那是他自己對於美感上,特意或是在過程中意外地留下的痕跡,他都會進行保留。最近的作品因為對於媒材的重視衍伸到對於媒材上面,剛剛賴志盛講的表面材質的痕跡、時間感、或是造型的接受,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並不意味著之前作品好或壞的問題,而是在於創作方式認知上的改變。我覺得現在的改變在於那個輕鬆度,他可以讓生活周遭進入到他的作品。在這系列裡面,我覺得在國立台灣美術館聯展《所在》,也在「外子」空間展覽是最明顯的一個轉變,這種轉變告訴我們你面對的是某一個石材或是某一道痕跡或是石材上面破面的造型,這種接受在你的創作歷程裡是一個比較大的轉換,會讓我們看到你作品裡面呈現更多的樣貌是因為當你面對各種石材或是石材狀況的時候,它就會對應出,對談出很多造型的可能性,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大的一個轉變。
我覺得在作品裡面有對於邊緣的注重,以前邊緣的存在似乎是在界定出你作品最邊邊的那個部分,但是你現在在邊緣的時候,好像處理的方式又不一樣,甚至它有時候並不是一個剩餘的痕跡,而是一個刻意的提醒,因為你有一些是畫線的、尤其是這個破裂面不是像以前這樣是一條直線要處理一個面出來剩下的,殘餘的鉛筆線或是簽字筆線,但你現在有點是要「提醒那個邊緣」,就是可以談談這些或是其他你想再談的部分。
詹士泰:可能跟自己從事這個工作的時間、跟自己現在所處的階段-就是自己的年紀(有關),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明顯我可以談的,就是對一些事情的包容,在生活當中所見所聞如果還可以有一些空間跟可能性可以去理解跟包容的話,我覺得我會試著去這麼做。所以在自己的工作、雕刻過程當中我覺得對材料來講,也是盡量去包容,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意外,這種意外不是指一個現狀的意外,有時候可能是心態上面會有一種意外的獲得。當我取得材料的時候,這幾年來的確在自己的工作上,對時間、對於一些生活上細微的種種,試著讓自己可以包容更多,像許遠達剛剛講的一種面和面之間延伸之後所推擠出來的一個末端,自己可以誠實的說,會希望在材料上面,是被我創作利用的材料。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大概在2011年之後,維持大概5、6年時間,我對我自己講,我的鉛筆線、我的記號、我的符號畫到哪,的手工就必須做到哪裡,也不見得就是一個左右的橫移或是一個上下的一個垂直水平,甚至可能是一個內凹的部分,因為做雕刻,比較難的,其實是做內凹。
所以我有段時間告訴我自己:沒得商量。我只要有一個初始的想法在,我就不能對自己有一種妥協,所以那個初始的想法出來之後,只要線一畫出來,我的手工,我的機器就是一定要推到那個點,然後中間不泛直角尺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去矯正,推到我要的那個點,一定要到位。這個時間,那種情緒也是自己告訴自己沒得商量,試著把你自己的可能性推到極限,我說極限當然跟古典雕刻的那種頭髮、手指頭的寫實的比擬,我覺得完全是不一樣的態度,那比較像是機械性的東西。在2018、2019之後,就會慢慢問自己:為什麼做?因為線到、手到、就一定機器要到的那個階段的尾端就是會問自己,那你如果只剩下一個命令跟一個動作必須要去達成的時候,那創作到後來情感的部分在哪裡?那突破性在哪裡?變成只剩一個類似像自我挑戰而已。後來就比較接近「外子」展覽之前大概兩年的時間,大概2018、2019的時候,我就開始省思一些問題,所以在「外子」那時候展覽當中比較後端的作品,意識到我自己個人的處境的當下是什麼樣的狀態。所以當過往40歲之前的自己,所在乎的會刻意排除掉一種人的溫度、生活中不確定性的態度,反而到40歲之後,我就開始做這樣的反思,接近這幾年下來,工作了二十幾年的時間,對這個材料我反而是花太少的時間在去正視的端看這個材料,所以這個材料的特質,是的確需要一個創作者去正視的問題,因為畢竟跟他相處的時間也不算短的時間。所以慢慢會覺得我反而可以包容這個材料,我取得的當下,它的原生狀態,它不見得是一個從礦區劈下來的裸石,而是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可能是上一個狀況之下所累積下來的、經過時間、空間的狀態因素條件,導致後來有一些時間的痕跡在上面,這樣的東西,當我取得的時候,我又可以用怎麼樣的態度去做一個比較輕鬆、比較正視的互動。
我覺得在作品裡面有對於邊緣的注重,以前邊緣的存在似乎是在界定出你作品最邊邊的那個部分,但是你現在在邊緣的時候,好像處理的方式又不一樣,甚至它有時候並不是一個剩餘的痕跡,而是一個刻意的提醒,因為你有一些是畫線的、尤其是這個破裂面不是像以前這樣是一條直線要處理一個面出來剩下的,殘餘的鉛筆線或是簽字筆線,但你現在有點是要「提醒那個邊緣」,就是可以談談這些或是其他你想再談的部分。
詹士泰:可能跟自己從事這個工作的時間、跟自己現在所處的階段-就是自己的年紀(有關),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明顯我可以談的,就是對一些事情的包容,在生活當中所見所聞如果還可以有一些空間跟可能性可以去理解跟包容的話,我覺得我會試著去這麼做。所以在自己的工作、雕刻過程當中我覺得對材料來講,也是盡量去包容,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意外,這種意外不是指一個現狀的意外,有時候可能是心態上面會有一種意外的獲得。當我取得材料的時候,這幾年來的確在自己的工作上,對時間、對於一些生活上細微的種種,試著讓自己可以包容更多,像許遠達剛剛講的一種面和面之間延伸之後所推擠出來的一個末端,自己可以誠實的說,會希望在材料上面,是被我創作利用的材料。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大概在2011年之後,維持大概5、6年時間,我對我自己講,我的鉛筆線、我的記號、我的符號畫到哪,的手工就必須做到哪裡,也不見得就是一個左右的橫移或是一個上下的一個垂直水平,甚至可能是一個內凹的部分,因為做雕刻,比較難的,其實是做內凹。
所以我有段時間告訴我自己:沒得商量。我只要有一個初始的想法在,我就不能對自己有一種妥協,所以那個初始的想法出來之後,只要線一畫出來,我的手工,我的機器就是一定要推到那個點,然後中間不泛直角尺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去矯正,推到我要的那個點,一定要到位。這個時間,那種情緒也是自己告訴自己沒得商量,試著把你自己的可能性推到極限,我說極限當然跟古典雕刻的那種頭髮、手指頭的寫實的比擬,我覺得完全是不一樣的態度,那比較像是機械性的東西。在2018、2019之後,就會慢慢問自己:為什麼做?因為線到、手到、就一定機器要到的那個階段的尾端就是會問自己,那你如果只剩下一個命令跟一個動作必須要去達成的時候,那創作到後來情感的部分在哪裡?那突破性在哪裡?變成只剩一個類似像自我挑戰而已。後來就比較接近「外子」展覽之前大概兩年的時間,大概2018、2019的時候,我就開始省思一些問題,所以在「外子」那時候展覽當中比較後端的作品,意識到我自己個人的處境的當下是什麼樣的狀態。所以當過往40歲之前的自己,所在乎的會刻意排除掉一種人的溫度、生活中不確定性的態度,反而到40歲之後,我就開始做這樣的反思,接近這幾年下來,工作了二十幾年的時間,對這個材料我反而是花太少的時間在去正視的端看這個材料,所以這個材料的特質,是的確需要一個創作者去正視的問題,因為畢竟跟他相處的時間也不算短的時間。所以慢慢會覺得我反而可以包容這個材料,我取得的當下,它的原生狀態,它不見得是一個從礦區劈下來的裸石,而是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可能是上一個狀況之下所累積下來的、經過時間、空間的狀態因素條件,導致後來有一些時間的痕跡在上面,這樣的東西,當我取得的時候,我又可以用怎麼樣的態度去做一個比較輕鬆、比較正視的互動。
「石子」詹士泰個展現場,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tone' Chan Shih-Ta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2)
許遠達:相信大家在詹士泰的分享之後你可以用他這個思考的路徑再返回去觀看他的作品,你可以發現出為什麼某些造型跟處理的方式會是這樣。另外一個部分,也稍微分享一下我地觀看,雖然之前有一些處理作品時他有刻意留下一些痕跡,但是這個痕跡可能比較像是過程的「紀錄」,而不是一種手感的溫度。但是現在的作品,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可以發現說,他會刻意在表面留下很多石頭機器、手磨、某種機器遺留下的人工的那個部分,因為這個關係,後來也運用機器打點的方式做了一些以打點來形成面的作品,那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會呈現出跟以前純粹造型時期的作品很大的差異性在於,作品本身所形成的質感會在觀看的過程裡帶給你某種手工的狀態,帶來溫暖。如果大家待會再仔細觀看的話,可以看到這些狀似非常幾何光滑的這種很絕對的面,它上面都留有很多來自於石材的狀態,和來自於人跟它相處過程中這個狀態的遺留,這個遺留跟以前的痕跡其實是有差異的,痕跡只是過程上面的一種紀錄。溫度上來講以前的東西比較冷一點,有點絕對造型的味道,那現在在每個處理過程裡面,都可以看到他嘗試把石材本身的溫度給表現出來,那我們再請賴志盛來講一下詹士泰在作品造型上面的一些觀察。
賴志盛:我自己在想,這工作它一定要有一種熱情是源自於他對這東西的愛,愛好,真正的愛這個工作,那如果說他只是為了完成一個造型、一個看起來像作品的東西,顯然我覺得在這裡頭它熱情一定不夠的,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屬於他自己很獨特的跟這個東西的感覺是一直不斷可以延伸跟長出來的才行。我也沒有什麼建議或說去討論關於這樣的工作,就是希望他能夠做更多、屬於他自己喜歡做的,對這東西的有愛人的方式去處理它。
詹士泰:賴志盛講的這個問題,我覺得終究還是會遇到,以前他有跟我提到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對我,或是一個創作者來講,可能都會是需要問的問題,可能不是學理的,不是很生硬的一種回答,他曾經問過我:「那你對你作品裡面、你對你自己的創作如果能夠能談得上是一種愛的話,那你的創作,覺得你那個部份是什麼?」我當時覺得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難,我當下整個腦經裡面速度晃得非常快,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東西是跟所謂「愛」有關的,然後很多很多的句子都跑出來,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關於情感關於愛的部分,我到現在還要很誠實地回答他很不容易,很難,但是如果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動力,是告訴自己我還可以這樣繼續做下去?我記得顧世勇老師曾經講,如果你只是為了完成而完成的話,他覺得這是很可悲的,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每天去工作室的一種習慣,縱使是掃掃地、把工具稍微整理一下、上上油什麼的,就是會很喜歡去工作室,那把材料放定位、把機器插了,開始去工作,這個動作好像表面上它又很像是一個慣性,是一個做創作的你就應該要每天一個時間到了你去工作室,然後我就開始在想,怎麼樣可以跟一種愛,能夠扯上關係。我後來回應他的一段就是說,我好像是一個對我所工作處環境的書寫,對一個周邊環境的描述,對於植物、對於竹林、對於風,對於我所踏的足跡的石礫、對於路面聲音的反饋,好像自己處在當下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你很想去做的,那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理出一個為什麼,但是會覺得自己對於去探尋材料、探尋某或是說對周邊環境身體的一個感知,那個當下伴隨著歲月、時間,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不曉得這個東西跟愛有沒有很接近,只是覺得,對於石材工作可能可以突破的,可能可以去實驗的,又或許有些東西可能只是有碰觸到但它的範圍還非常廣泛,所以覺得還能做的、還沒做到的,還很多。
賴志盛:我自己在想,這工作它一定要有一種熱情是源自於他對這東西的愛,愛好,真正的愛這個工作,那如果說他只是為了完成一個造型、一個看起來像作品的東西,顯然我覺得在這裡頭它熱情一定不夠的,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屬於他自己很獨特的跟這個東西的感覺是一直不斷可以延伸跟長出來的才行。我也沒有什麼建議或說去討論關於這樣的工作,就是希望他能夠做更多、屬於他自己喜歡做的,對這東西的有愛人的方式去處理它。
詹士泰:賴志盛講的這個問題,我覺得終究還是會遇到,以前他有跟我提到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對我,或是一個創作者來講,可能都會是需要問的問題,可能不是學理的,不是很生硬的一種回答,他曾經問過我:「那你對你作品裡面、你對你自己的創作如果能夠能談得上是一種愛的話,那你的創作,覺得你那個部份是什麼?」我當時覺得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難,我當下整個腦經裡面速度晃得非常快,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東西是跟所謂「愛」有關的,然後很多很多的句子都跑出來,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關於情感關於愛的部分,我到現在還要很誠實地回答他很不容易,很難,但是如果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動力,是告訴自己我還可以這樣繼續做下去?我記得顧世勇老師曾經講,如果你只是為了完成而完成的話,他覺得這是很可悲的,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每天去工作室的一種習慣,縱使是掃掃地、把工具稍微整理一下、上上油什麼的,就是會很喜歡去工作室,那把材料放定位、把機器插了,開始去工作,這個動作好像表面上它又很像是一個慣性,是一個做創作的你就應該要每天一個時間到了你去工作室,然後我就開始在想,怎麼樣可以跟一種愛,能夠扯上關係。我後來回應他的一段就是說,我好像是一個對我所工作處環境的書寫,對一個周邊環境的描述,對於植物、對於竹林、對於風,對於我所踏的足跡的石礫、對於路面聲音的反饋,好像自己處在當下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你很想去做的,那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理出一個為什麼,但是會覺得自己對於去探尋材料、探尋某或是說對周邊環境身體的一個感知,那個當下伴隨著歲月、時間,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不曉得這個東西跟愛有沒有很接近,只是覺得,對於石材工作可能可以突破的,可能可以去實驗的,又或許有些東西可能只是有碰觸到但它的範圍還非常廣泛,所以覺得還能做的、還沒做到的,還很多。
左:藝術家工作室
右:詹士泰 Chan Shih-Tai, Untitled 無題, 2020, sedimentary rock 沈積岩, 29.5×27.5×5cm
右:詹士泰 Chan Shih-Tai, Untitled 無題, 2020, sedimentary rock 沈積岩, 29.5×27.5×5cm
許遠達:我之前在策劃「所在」展覽的時候,有邀請詹士泰來參與,那個展覽講的是材料跟空間在1980年代開始的一些藝術到現在創作者相關,有這種取向的創作者的展覽,會想到請詹士泰來展覽是說,我發現之前好像有聽你講,你幫賴志盛製作筆記本的時候的,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迷人的關於創作者跟他使用媒材的極限的那種對話,那是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詹士泰:我剛到南藝大工作室估做的時候,那時候剛好碰巧賴志盛他有請我幫忙做了幾件活頁紙的作品,然後這東西也對我後來在創作上有一個很大的影響跟一個啟發點,過往我比較少去把作品處理到這麼薄。他當時跟我說是0.5公分,就是0.5公分厚的一包活頁紙,然後他要我去找一塊白大理石,然後幫他處理這樣,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ok我試試看,所以後來在處理過程當中遇到一些問題,也是我以前沒有碰過的。我試著幫他抓,從一公分,慢慢抓到0.6,慢慢往下降,降到差不多0.5的時候,因為它有一個面積,就是當我們機器在上面拋的時候,因為通常機器鉅片磨片在上面打、在上面摩擦在旋轉的時候,那個溫度會瞬間拉很高,但是又不能夠太高,高到讓大理石它的結晶會改變,有點類似像燒焦,所有的結晶會分開,它也不是裂但它的結晶彼此之間會產生就像疤痕一樣,變成看起來不完整,你摸起來不會覺得說有什麼改變,但它看起來結晶變得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在幫他處理的時候,就發現到,我當時有幫他處理一個問題就是,機器在拋溫度一高的時候,我有加水,然後一加水的時候,溫度降了可是每做一個動作拿直角尺去測,很奇怪就是0.5公分的時候,厚度已經算很薄了,結果,直角尺一放下去,竟然兩邊是高起來的、中間是凹下去的,甚至是會多過於0.5公分,我當時就不敢相信,左右邊都是0.5公分,整個石頭都是0.5公分可是它卻中間會凹下去超過(低於吧)0.5公分,所以我就覺得不太對,後來才知道,石頭當溫度高的時候,水一加下去的時候,它整個石頭,是翹起來的,就是在約略是A3大小,然後它那個石頭0.5公分的時候,整個溫度是拉高的,我當時覺得這樣子的狀況下會不會整個石頭會出問題,因為它的彎曲度太大了,怕它會產生裂痕這樣,結果是慢慢的把它救回來,後來也慢慢的降溫之後,再細微的用手工處理,因為機器的速度很快,溫度瞬間拉很高,所以我後來改成用手磨到一個平整的程度。從那次之後,我在作品上是有試著給自己一些可能性去處理可能這樣子的作品,如果石頭是脆,那你可以試著磨到0.3、0.2甚至它裂痕出來的時候,也許這個當下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跟結果,所以從那次做的0.5公分之後,其實到後來,也給我一些在創作上的嘗試,最明顯就是,待會大家可以看就是最靠近玻璃那件,放在木箱上,薄度就是接近0.5公分。
許遠達: 請大家鼓掌謝謝詹士泰帶來這麼好的分享。
詹士泰:我剛到南藝大工作室估做的時候,那時候剛好碰巧賴志盛他有請我幫忙做了幾件活頁紙的作品,然後這東西也對我後來在創作上有一個很大的影響跟一個啟發點,過往我比較少去把作品處理到這麼薄。他當時跟我說是0.5公分,就是0.5公分厚的一包活頁紙,然後他要我去找一塊白大理石,然後幫他處理這樣,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ok我試試看,所以後來在處理過程當中遇到一些問題,也是我以前沒有碰過的。我試著幫他抓,從一公分,慢慢抓到0.6,慢慢往下降,降到差不多0.5的時候,因為它有一個面積,就是當我們機器在上面拋的時候,因為通常機器鉅片磨片在上面打、在上面摩擦在旋轉的時候,那個溫度會瞬間拉很高,但是又不能夠太高,高到讓大理石它的結晶會改變,有點類似像燒焦,所有的結晶會分開,它也不是裂但它的結晶彼此之間會產生就像疤痕一樣,變成看起來不完整,你摸起來不會覺得說有什麼改變,但它看起來結晶變得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在幫他處理的時候,就發現到,我當時有幫他處理一個問題就是,機器在拋溫度一高的時候,我有加水,然後一加水的時候,溫度降了可是每做一個動作拿直角尺去測,很奇怪就是0.5公分的時候,厚度已經算很薄了,結果,直角尺一放下去,竟然兩邊是高起來的、中間是凹下去的,甚至是會多過於0.5公分,我當時就不敢相信,左右邊都是0.5公分,整個石頭都是0.5公分可是它卻中間會凹下去超過(低於吧)0.5公分,所以我就覺得不太對,後來才知道,石頭當溫度高的時候,水一加下去的時候,它整個石頭,是翹起來的,就是在約略是A3大小,然後它那個石頭0.5公分的時候,整個溫度是拉高的,我當時覺得這樣子的狀況下會不會整個石頭會出問題,因為它的彎曲度太大了,怕它會產生裂痕這樣,結果是慢慢的把它救回來,後來也慢慢的降溫之後,再細微的用手工處理,因為機器的速度很快,溫度瞬間拉很高,所以我後來改成用手磨到一個平整的程度。從那次之後,我在作品上是有試著給自己一些可能性去處理可能這樣子的作品,如果石頭是脆,那你可以試著磨到0.3、0.2甚至它裂痕出來的時候,也許這個當下會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跟結果,所以從那次做的0.5公分之後,其實到後來,也給我一些在創作上的嘗試,最明顯就是,待會大家可以看就是最靠近玻璃那件,放在木箱上,薄度就是接近0.5公分。
許遠達: 請大家鼓掌謝謝詹士泰帶來這麼好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