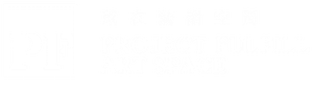從感知整體到意義整體:張允菡的《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
作者|王柏偉,原文刊於《週刊編輯》四月份
張允菡獲得2018年台北獎優選、在北美館展出的《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一作,是她2014年在The Arctic Circle 極圈短期駐村計畫之後所做的作品,曾於2015年於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展出過,不過與這次在北美館展出的形式不盡相同。
在北美館的白立方空間中,藝術家在大面落地窗貼上透光的、極地丘陵搭配著大片雪地的景致,這面景致隨著窗外天色的改變而改變它的氛圍。在這佔滿整個牆面的景致前,垂掛著由霓虹燈管彎成的「Place」大字。與這面引人注目的大型牆面相對的,是一個掛在天花板風管底端,多數觀眾如果沒有特別在意展場細節就一定會忽略的小型圓框,是在北極時從船上窗戶向外看出去的景象。展場牆面上滿佈文字,除了入口處創作論述式的簡短說明之外,其他都是由張允菡親自將當時的日記手寫在牆面上。展間中玻璃架子上,則陳列著一張又一張由張允菡口述、插畫家廖怡惠重新組織過的北極意象。當年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展覽中,大牆面北極景致由於位在地下室,所以並無天光得以依憑,繪畫作品則如橫幅捲軸般地掛在如船體結構的柱子間。
感知的整體,而非觀念
乍看之下,這樣的作品形式與觀念藝術類作品的展示風格有點類似。約瑟夫・科蘇斯(Joseph Kosuth)的觀念藝術名作《一把椅子與三把椅子》在展場中靠牆處放置了一把木製的椅子,並在椅子的左右分別掛了這張椅子的照片與百科全書上關於椅子的說明辭條,藉此指出「藝術」強調的是如何用不同的媒材來表達「觀念」。《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看似也是藝術家藉由文字、影像與裝置來處理對於「北極」不同面向,難道張允菡是將「北極」看成一個必須要用不同媒材加以展示的「觀念」嗎?
藝術家有一次在攝影空間Lightbox的座談中提到,當她面對北極那樣巨大的、沒有太多人工斧鑿痕跡的對象的時候,原本對於北極的想像,甚至是作品要做什麼的計畫,都失去了原來的重量。時間感整個改變了,時間變的很長也很多,沒有太多必須要馬上回應的事情,甚至,在這樣蒼茫一片的白色大地中,連人都變的非常渺小。對於張允菡來說,到底「藝術」之於北極的意義是什麼?甚至,到底「人」之於北極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兩個問題從她踏上北極的那一刻起迄今,一直都縈繞在她的心中。從這點來看,《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的問題意識全然不同於科蘇斯那種觀念藝術的出發點,而是回到歷史上更為久遠的、從「感知學(aesthetics)」的發端到「藝術(art)」之所以成形的那個時代。
現代意義下哲學所談論的「感知學」,中文往往翻譯成「美感」或「美學」,是西方十八世紀的產物,出現的背景是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興起的時刻。在經歷文藝復興之後,「人」在世界與歷史上的地位從宗教性的「彼岸」與「永恆」掙脫開來,開始具有「現世」的價值,甚至可以開始「創造」意義。在這個強調「人」具有創造能力的時期,在「感知」層面上,「人」也必須被視為是獨立的、是具有個體性的,換句話說,每個人在感知層面上都可以是不同於其他個體的,也只有這樣,屬己的意義創造才得以可能。正是每個個體都有不同於其他個體的感知內容與方式,所以探討不同個體彼此之間「感知整體」上差異的「感知學」就出現了,當這樣一個哲學的分支進一步在十九世紀專業化成為一門學問時,「藝術」就產生了,同時期一併產生的還有現代意義下的「科學」。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允菡在北極思考藝術與創作的意義時,認為藝術家與探險家、科學家一樣,都是透過個體所感知到的內容來傳達「另一個世界」(北極)的內容。
文字、影像、繪畫與裝置的同步化
對於「感知整體」的強調,分別可以從兩個作品中的元素看得出來。張允菡選擇用手寫的方式對照著留在手機中的圖片,選出幾則日記寫在白色的牆面。在機械複製時代再次強調「視覺→腦→手」的生產方式,堅持的是不被自動工具全然決定的「個體性」,是一種將「感知整體」轉化成「意義整體」的自主性強調。與此類似的強調,就在藝術家將北極之旅前後查找的相關資料與故事,跟插畫家朋友朋友分享,並且經過插畫家自身的理解與詮釋之後,成為我們在展場中所看到的這些繪畫作品。這些作品有些是她們兩人共同分享的故事,有些是廖怡慧轉化之後對北極的想像。張允菡特別強調,這樣的合作關係所產出的圖像,不是一種插畫式的圖說,而是另一個人聽到她的北極經驗後的再轉化。對我們來說,這恰恰不同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攝影簡史〉中對於影像大量複製時期「圖說」重要性的強調。班雅明強調影像過剩的問題必須依賴圖說來解決,但誠如謝佩君在〈從後自然到後媒介性:從新物質主義看「2018台北美術獎」〉這篇文章中,以「放大」來指稱張允菡的「不插電」行為的做法,我們在《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中所看到的,影像、文字、裝置、繪畫…等不同媒介之間之所以能具有「同步性(synchronization)」,並指向「北極」這個位置(Place),是因為藝術家在意的仍然是:「感知」必須作為一種資訊的過濾器,才能為「人」這種意義生產器化約外在環境的複雜性,不管這個外在環境所給出的是不是像北極一樣,是巨大的、意義缺乏的焦慮。
在北美館的白立方空間中,藝術家在大面落地窗貼上透光的、極地丘陵搭配著大片雪地的景致,這面景致隨著窗外天色的改變而改變它的氛圍。在這佔滿整個牆面的景致前,垂掛著由霓虹燈管彎成的「Place」大字。與這面引人注目的大型牆面相對的,是一個掛在天花板風管底端,多數觀眾如果沒有特別在意展場細節就一定會忽略的小型圓框,是在北極時從船上窗戶向外看出去的景象。展場牆面上滿佈文字,除了入口處創作論述式的簡短說明之外,其他都是由張允菡親自將當時的日記手寫在牆面上。展間中玻璃架子上,則陳列著一張又一張由張允菡口述、插畫家廖怡惠重新組織過的北極意象。當年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展覽中,大牆面北極景致由於位在地下室,所以並無天光得以依憑,繪畫作品則如橫幅捲軸般地掛在如船體結構的柱子間。
感知的整體,而非觀念
乍看之下,這樣的作品形式與觀念藝術類作品的展示風格有點類似。約瑟夫・科蘇斯(Joseph Kosuth)的觀念藝術名作《一把椅子與三把椅子》在展場中靠牆處放置了一把木製的椅子,並在椅子的左右分別掛了這張椅子的照片與百科全書上關於椅子的說明辭條,藉此指出「藝術」強調的是如何用不同的媒材來表達「觀念」。《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看似也是藝術家藉由文字、影像與裝置來處理對於「北極」不同面向,難道張允菡是將「北極」看成一個必須要用不同媒材加以展示的「觀念」嗎?
藝術家有一次在攝影空間Lightbox的座談中提到,當她面對北極那樣巨大的、沒有太多人工斧鑿痕跡的對象的時候,原本對於北極的想像,甚至是作品要做什麼的計畫,都失去了原來的重量。時間感整個改變了,時間變的很長也很多,沒有太多必須要馬上回應的事情,甚至,在這樣蒼茫一片的白色大地中,連人都變的非常渺小。對於張允菡來說,到底「藝術」之於北極的意義是什麼?甚至,到底「人」之於北極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兩個問題從她踏上北極的那一刻起迄今,一直都縈繞在她的心中。從這點來看,《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的問題意識全然不同於科蘇斯那種觀念藝術的出發點,而是回到歷史上更為久遠的、從「感知學(aesthetics)」的發端到「藝術(art)」之所以成形的那個時代。
現代意義下哲學所談論的「感知學」,中文往往翻譯成「美感」或「美學」,是西方十八世紀的產物,出現的背景是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興起的時刻。在經歷文藝復興之後,「人」在世界與歷史上的地位從宗教性的「彼岸」與「永恆」掙脫開來,開始具有「現世」的價值,甚至可以開始「創造」意義。在這個強調「人」具有創造能力的時期,在「感知」層面上,「人」也必須被視為是獨立的、是具有個體性的,換句話說,每個人在感知層面上都可以是不同於其他個體的,也只有這樣,屬己的意義創造才得以可能。正是每個個體都有不同於其他個體的感知內容與方式,所以探討不同個體彼此之間「感知整體」上差異的「感知學」就出現了,當這樣一個哲學的分支進一步在十九世紀專業化成為一門學問時,「藝術」就產生了,同時期一併產生的還有現代意義下的「科學」。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允菡在北極思考藝術與創作的意義時,認為藝術家與探險家、科學家一樣,都是透過個體所感知到的內容來傳達「另一個世界」(北極)的內容。
文字、影像、繪畫與裝置的同步化
對於「感知整體」的強調,分別可以從兩個作品中的元素看得出來。張允菡選擇用手寫的方式對照著留在手機中的圖片,選出幾則日記寫在白色的牆面。在機械複製時代再次強調「視覺→腦→手」的生產方式,堅持的是不被自動工具全然決定的「個體性」,是一種將「感知整體」轉化成「意義整體」的自主性強調。與此類似的強調,就在藝術家將北極之旅前後查找的相關資料與故事,跟插畫家朋友朋友分享,並且經過插畫家自身的理解與詮釋之後,成為我們在展場中所看到的這些繪畫作品。這些作品有些是她們兩人共同分享的故事,有些是廖怡慧轉化之後對北極的想像。張允菡特別強調,這樣的合作關係所產出的圖像,不是一種插畫式的圖說,而是另一個人聽到她的北極經驗後的再轉化。對我們來說,這恰恰不同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攝影簡史〉中對於影像大量複製時期「圖說」重要性的強調。班雅明強調影像過剩的問題必須依賴圖說來解決,但誠如謝佩君在〈從後自然到後媒介性:從新物質主義看「2018台北美術獎」〉這篇文章中,以「放大」來指稱張允菡的「不插電」行為的做法,我們在《其實我們什麼也不是》中所看到的,影像、文字、裝置、繪畫…等不同媒介之間之所以能具有「同步性(synchronization)」,並指向「北極」這個位置(Place),是因為藝術家在意的仍然是:「感知」必須作為一種資訊的過濾器,才能為「人」這種意義生產器化約外在環境的複雜性,不管這個外在環境所給出的是不是像北極一樣,是巨大的、意義缺乏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