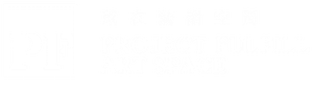論周育正近期的一些提案
文╱陳璽安 (刊登於今藝術2013年六月號)
藝術觀眾如何閱讀周育正的創作,是筆者一直觀察的問題。一方面,「精準的問題意識與展示操作」使他囊括大大小小的獎項,評論如是說;另方面,關於周育正,我們好像只有幾個版本相似的解讀與批評。這趟必要的智識旅程因此成行,始於藝術家近期的個展《易雅居Yi&C.》,結束於藝術家隱而未顯的創作議程中。
在我們真正走入周育正於就在藝術空間的個展之前,會看到一個回憶錄式的展覽介紹。裡面簡單描述了藝術家在多年後與第一次賣出之作品重逢的陌生感。這些整批被收購的作品因為轉手的原因需要簽名。比較起來,這段文字也許沒那麼像一般看到周育正的創作時就視覺感受上那樣的冷洌,反而有點朱天心式的荒涼。
展場中的作品除了在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時製作的《TEMCO》以外,另有一件放在展場算是中央位置的新製作。以展覽介紹提到的經驗為引子,周育正發展出《自由生產》這組作品,由掛在牆上的空白畫布以及鄰近白色櫃子中平放著的一系列繪畫組成。作品出售的機制是一張空白畫布配上一張被收納著的方形畫作。裡面描繪的是一旁空白畫布被收購者繪製成為單色畫後的立體模擬圖。其實,即便有買下的收藏家真拿著周育正調好的顏色將作品完成,這樣的參與性質實際上也只是種表面的說法。反而是收藏者若真在他的畫作上覆蓋一層顏料,將負擔起作品不容易轉手的風險。問起周育正,是否當藏家沒依照他的規則處理他們買到的畫作,這件作品成立的契約就會失效。不過,他並沒有意要設定出這類複雜的合約。真正說起來,當他用上展覽介紹絕大部分的篇幅,鋪陳一個關於作品與藝術家各自有其際遇的回憶,而不再將展覽在觀念上設計成奇特的等式,似乎說明著這件作品更著重於想像層面上的生命歷程。用藝術家自己的話來講,他希望創造的是「思考物件」,而非我們以往所熟悉的那個斟旋在幾個機構之間,揭露資源流動的作品形象。
其實,早在周育正製作《虹牌油漆》及《東亞照明》的階段,就有論者對其變換不定的創作形象有所說明。在《關於周育正最近轉向的一些細節》一文中,徐建宇表明藝術家不斷自原先創作路線離去的「轉向」其實也只是「對自身生存感的回應」。不過,這樣的概括性說法並不能幫助我們瞭解一些至關重要的鑑賞前提:周育正以提案處理資源問題創作方法本身是否具有特定機制批判的指向,又或者,這樣風格化的語彙能夠應用在任何題材上,舉凡藝術家之記憶、家庭情景以至於社會交往的經驗?
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談起周育正於密集的展覽行程中持續擴展的主題了。這不僅僅是轉向與否的問題,而是關係到藝術家如何將新的事物混在以往的語言之中表達出來。而這篇文章要做的工作,便是從這場個展中的一個裂縫進一步獲得上述問題的解答。這個裂縫與展覽介紹有關:作為認識本次製作的入口,它那荒涼傷感的調子與它所指涉的作品《自由生產》在視覺與觀念上的狡慧之間,是否有個銜接不上的落差,從而暗示了未完成的創作議程?
大家說起周育正透過提案作為創作主要方式的時間點,應是從2009年參與賑災義賣所製作的版畫開始。其實,我們不該只以「提案」來概括一個藝術家創作的主要方式,其籠統程度不下於在所有人都畫畫的時代將一個創作者描述為畫家。因為整個藝術世界已經透過策展、補助、獎項等機制,使得每個當代的藝術實踐至少在原則上都隱含了以提案為存在形式的前身。然而,即便提案已經成為整個創作活動的流程裡一個普遍運用的工具,它在很多情況下仍往往被使用者忽略。實際上,就連去參加一場展覽開幕時跟同行口述到自己即將進行的創作,都算得上某個程度的提案。因為大家都清楚,短短幾句話的效益將可能為一個還未實現的作品帶來新的社會關係。周育正近年來有意識地標明藝術家所棲居的社會情境,大抵是就此而言。
在訪談中,周育正也提到本次《自由生產》的畫作內容,與先前一部分的創作所使用的規則相同,都只是種存在形式的指涉,而非特定內容的再現。周的提案剛好就是這麼一門方便的工具:它能夠讓藝術家在創作上跳過視覺語言的中介,將關注的事物直接寫到他的遊戲規則之中。作品內容是可被替換的這件事當然有它的反面,這讓我們看到類似的遊戲規則可能出現在對象不同的兩件作品上。若細細追究起來,當《虹牌油漆》及《東亞照明》實際上使用了同一個規則時,則它們各自的內容——其批評或者提出之事物的差異——又代表了什麼呢?
近期,王咏琳的文章《作品內容飛翔在藝術形式的翅膀上》進一步將周育正的近期創作區分為關乎「空間」的提案與關乎「人」的提案。說起前者,人們多談到其資源重新分配的美學。這樣的手法看似批判性的體制檢驗,但真要細究起來,其中的資金零和循環更像是拿砝碼在天平兩端測試平衡感的測量;這個資源流動的等價美感,帶點fine art的品味標準,是這類作品獲得褒揚的原因之一。而從特定場合的概念延伸而來,資源本身直接出現在作品內容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其具體的形象也框限了藝術作品閱讀的可能性。就這個角度而言,精細「設計」過的創作,大概不會是周育正作品中層次最為豐富的系列。我的建議是,應以作品閱讀層次的觀點看待近期發展出來的另一提案系列。如周育正提給北美館策劃展《真真》的新製作《提案》中,印表機在昏暗的燈光下徒勞而重覆地列印出一件件未及成型就已被遺棄的作品。也許你可以說這仍然有種自我指涉的成分。然而,迥異於一般「設計詭計」指導下的產品,將許多無名的提案放上展覽的想法所提出的不再是資源流不流動的問題了:它們少了遊戲的意圖,帶有點提案本身生命史的指涉。正是在這類型的創作中,沒那麼貼近議題形象的指涉物讓閱讀作品的空間才又落回我們這些觀眾身上,並得以將作品投射在與宏觀的社會實景。
《自由生產》算得上是這樣的作品嗎?它看上去仍像是對藝術家的資源流動重新想像的工作,但拿掉了封閉的公式。而要求收購畫作者必須在作品交易之後將買到的一件作品上色的來由,顯然是從展覽介紹提到的那個故事改編而來。以提案的形式,將作品離開藝術家後的飄流呈現在作品面貌的改變上。我不確定藝術家是否成功說明了這件事情,單單能夠肯定的是新舊語彙夾雜在這件作品的狀態。在這個轉折的過程中,有個自《工作史—盧皆得》、《提案》以來還沒被藝術家透過創作來完整標明的,關於作品與生命之議程。用《自由生產》的話來說是這樣的:在創作的路上有時會發現作品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般,其身體會老舊、毀壞;有可能因為其議題與往後社會發展的節拍而時來運轉;或有生不逢時無人聞問的可能;也許轉手的某些時刻會與藝術家重逢。而這些事都已經超出藝術家當初創造它的權限了。像是藝術家以《工作史-盧皆得》保留父輩的一段記憶,計劃持續發展並迎來他與盧先生意料之外的展覽邀約一般。而這些旅程,可不是計劃與提案可以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