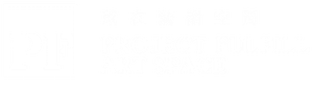心識的實體 ─ 吳東龍「屈尺」個展
文/高子衿
我們應該改變事物的順序:第七天應該是人類勞動的日子,在這一天以額上的汗水賺取生活所需;其餘六天則作為感性和靈性的安息日,漫遊在廣袤的花園裡,啜飲大自然溫柔的感化和崇高的啟示。
~享利.梭羅(Henry D. Thoreau,1817-1862)
吳東龍到台南藝術大學造形所之前的作品,與空間有些關係,但多半還是以視覺上具體的關係例如內外去談,使用的顏色與畫面上具指向性的線條也較多;進入南藝之後,除了最為明顯的從城市喧囂急轉為安靜的鄉間生活,最重要的是居住環境的尺度結構亦已截然不同。無論是提供師生住宿的校園型大學,或是學校地處的鄉鎮,皆是以人們步行能夠抵達的距離為邊界範圍,當中,建築物呈不規則混雜配置,而其量體和四周的景物則合乎人類的視覺尺度,故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中,一個非侵略性且適合居住的微縮聚落。
大小適宜的地理空間,除了在實際生活面向上獲得舒坦的餘裕,同時也因為能夠掌控在樹叢、建物等視覺障礙之後的空間為何,以及反推知曉自己當下所處的位址,都增加了生活於此一空間的安全感。這樣的感受雖然亦可能發生於大城市居民對於自己生活鄰里的熟悉,然而幅員遼闊的都會,猶如疊生多層於花托上的複瓣花朵,在你所熟悉的區域之外又朝向四方連結了陌生的文明環境,使得人們在當中因為未能有明確的座標參照,故而自我仍一再受到外在變因的影響。
驟變的場所特性對於吳東龍的創作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並逐漸確立某些今日我們所熟悉的畫面處理方法,例如作品抽離掉對於外在事物的形體描繪,畫面只留下對透視法反動下的純粹線條、色彩和二度空間,構圖也確定為因四面力量均衡,使得漂浮物體位處於中央的方式;而將物體以全景式的剖面手法展現,則體現出一種對於事物的清楚觀看。此外,至鄉間尋找適合人類活動的居住可能,一次收攏自然與文明的優點,似乎也呼應了作品中種種並不傾斜某端的雙生結構,例如為了成就背後感性的理性表象、平塗表面而刻意留下的畫布紋理(繪畫與其物質性),或是主體與背景的相反相成關係等。
結束於台南的居住後,吳東龍在一次實地走訪下,發現位於新店屈尺的一層老公寓,一待轉眼就是五年。「屈尺」這個頗令人玩味的地名來源眾說紛紜,有一說認為因山巒環繞、周高中低,故而由「窟石」得名;又或有人取其文字意涵,認為「屈尺」便是描繪此處溪水所形成特殊的直角屈曲。雖然離新店市中心只有五公里遠,但因為地理環境的封閉因素,以及位於水源保護區內的建設管制,因而至今仍保持中南部小農村特有的緩慢步調。簡單的道路、單純的住戶,投射予居住在此之人一種安定的精神力量。反映之於創作,則「因為環境的簡單,在這生活與工作的步調也維持一定的緩慢,更能夠深入且仔細處理或感受每一個步驟,像是基底材的準備與處理,以及色彩的層次與深入感知等。」
在鄉間獨居,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思索和親近大自然,其中重要意義並不在於自我摒除於經濟生活之外,而是吳東龍借用了屈尺的清靜,來正視心靈生活及進行創作。特別的是,吳東龍先後所待過的這兩個地方,與梭羅寫下知名文學著作《湖濱散記》(Walden Pond)時所居住的瓦爾登湖畔近似,環境中都有湖泊(珊瑚潭和梅花湖)這樣的自然景象,此種反覆出現的環境因子,不能僅被視為巧合,而該究竟其某種意識上的聯繫。梭羅認為:「湖是風景中最美的、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著它的人可以測出自己天性的深淺。」讓自然萬物在此棲居的湖泊,同時體現自然對人的精神淨化,以及對於工業文明的批判,作為一個具有時間感卻不受傳統、文明意識拘束的「巨大貯存槽」,其特性可以在吳東龍的作品中發覺到相為對應的意象:居於直覺世界與理解世界之間,也就是不偏頗於感性或理性光譜任一。
一件作品若深入剖析,可發掘出由敍述表層和由原型組成的深層結構。屈尺的四季景觀分明,夏季生意盎然,經過冬寒料峭又回到春天的萬象一新,再加上源源不絕的溪水,不但充滿了變化,也帶來能洗滌煩悶人心、得以重生之永恆期待。然而吳東龍的作品並非直接指涉這些自然景象,而是藉由藝術家的詮釋和語言創造進行轉化,例如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慣用的藍綠色系暗示了生命的存在,而觀察自居室窗外漫山的濃淡綠意,則再現為以極細微的筆觸在畫面上進行深色的暈染,既讓原來平均明晰的視覺厚度產生輕微的變化,也破除帶有權限範圍和數學性圖形的純粹自律。又或是在「Color Lines」系列《06》和《07》兩件作品中,底層變化充滿了明顯情緒感,是自2008年以來第二次背景採用不同顏色的嘗試,然而為了平衡力量,將鄉居中來自於雨滴、風勢強弱的感受,以同樣極少使用的黑紅重色,轉化成不同節拍的理性長短線條。
圖像產生並非藉由重複塗繪的動作得來,在吳東龍的創作手法中,帶有極度對於「減除」的推崇,有時是以空筆帶走畫面上的顏料;有時是在重複上膠,將布目空隙填滿、做完打底的工作之後,仍堅持保留透顯畫布質感;又或是近期領略到甚至連色彩也可以從事刪減的動作,故而進行輕薄且具穿透性表現的嘗試。吳東龍認為,一般人渴求能從繪畫中得到所有,「我則希望藉由單純色彩便能給予飽滿回饋,因為越純粹所能給予之物,反倒可能是更為豐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