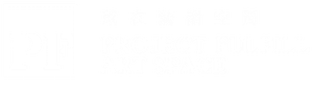有星星、微風的夜晚—談王璽安的繪畫創作
文╱蘇俞安
時常思考何謂作品中的「當代性」?瀏覽現今藝術評論,絕大部分的「當代性」為凸顯當今文化現象或新媒體之新技術運用。台灣當代繪畫的作品討論則偏向圖像與媒體影像運用或繪畫內容上著墨,較少看見有關繪畫本體論的思考與探討,例如材質操作機制與畫面構成等。王璽安的創作則隱約顯露對繪畫本體論的思考,其中包含作品的構成與圖像意義。而這種不斷對約定俗成的藝術(繪畫)法則反思與檢視,最早從立體主義開始讓繪畫產生劇烈的變化。
由於希望獲得理想的比例,不再受人類的局限,這些年輕畫家獻給我們的作品中,腦力要比感性強。他們為了表現形而上的那種恢弘,越來越摒棄視覺幻像和局部比例的古老藝術。
藝術發展自立體主義開始,一些畫家極力想擺脫繪畫的制式法則,即從文藝復興以來所遵從的透視法,但在擺脫的同時,也承認自身與傳統的關係,那是一種相對的辯證關係。從而開始,一條理性檢視與反思藝術體系或創作架構的思維啟萌,而璽安的創作,自許將繪畫的「形象變成元件一般的東西,繪畫就是將這些元件組合在一種人類行為中得於藝術脈絡繼承的操作,所以在繪畫的時候,就是對於這些被視為元件的圖形作一種安排」。[1]因此藝術史對璽安的創作有著重要的思考與影響。
藝術家們拿著現代主義的旗幟,各自朝向不同的方向摸索與發展,但在繪畫中似乎可以隱約概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直覺式的創造,類似表現主義或原生藝術(Art Brut),強調作者內心世界,畫面衍然是精神的意識流動,觀者可以從顏色與筆觸感受到作者情緒的流動,作品從而與作者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另一類型是用哲學的態度來思考作品或媒材本身的藝術命題,璽安便是會分析與觀照所使用媒材的語彙,使他的作品與其他用繪畫創作的台灣藝術家不同。作品不僅僅是敘述式或表現式,而是一種更為形而上的所思與展現。
構成的營造
璽安經歷過藝術學校的傳統繪畫訓練,在訪談中表示不想再做類似傳統美術比賽中填滿畫面的作品,這使他對於畫面的構成採取不同的思維。這些作品皆淡化主題與背景的關係,使畫面結構鬆開,主題卻變得明顯突出而圖像化。由於畫面結構鬆開,改變我們觀看繪畫的習慣,並讓他的畫面像中國山水畫般悠遠安靜。
觀看<黃色裡的紅三角>,乍看以為是描繪山坡上的鄉村景象,但仔細看發現可能是同一座建物不同方向的描繪練習,也有可能它們是不同的建物,彼此散落於各處。相似的東西透過大小與樹叢前後的對照,向觀眾暗示這個或這群建築物的空間位置座落關係。也由於主題與背景觀關係鬆開,使畫面可以做非單一透視的表現。
另一種座落對照空間的表現是<上面有紫色的星星>,具體而詩意地顯現我們與星星的位置,使他的作品帶有一種超乎個人、世俗,而是與萬物乃至宇宙有空間上的連結關係。
這些符號的限度為我們架構了某種道德與美學的描繪法規;更甚者,在靈視的繪畫中,我們架構出了事物新的形而上心理狀態。一件物體在畫中必佔有的那種絕對的空間意識,以及將物體彼此分開的絕對空間意識,建立了一種新的事物天文學,以地心引力這首要法則依附於地球上。面積和體積上的分毫不差,並仔細測定過的使用構成了形而上美學的準則。
基里訶(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於1917年成立形而上畫派,他喜愛希臘建築中嚴肅、奧秘的自然法則。他的作品把生活場景與物件重新組成,透過經心的安排使畫面表現象徵(sign)意義的孤立,傳達出難以言說的神秘詩意。璽安的作品也是將描繪對象在他所設定空間展開,這種意義的不明確或象徵意義的孤立,多少使他的作品帶有一種疏離感與觀看經驗中新的可親性。
超越智識理解與功能意義的圖像語彙
如何將事物的意義準確地呈現在繪畫當中?繪畫始終具有傳達意義的不完整性,例如平面性與作者選擇性的觀看位置等。璽安為傳達繪畫圖像意義的不完整性,於是在<綠色裡的三種樹>與<黃色裡的紅三角>拆解成一團顏色或一個色塊、一個形象或幾何的造形,而不是單一欣賞一棵樹或一棟建築物。
然而若繼續追究事物的意義,有可能因過於熟悉而被隱藏,如馬格利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所探討圖象或文字中傳達意義的危機,我們很容易透過專斷的語言系統誤解事物真實的面貌。馬格利特喜愛透過畫面與現實經驗中的矛盾性,呈現不穩定與非語言可掌握的現象。璽安的作品也常思考形象與物質意義的關係,例如<灰白色裡的兩種覆蓋>,巧妙地在畫面同時出現兩種意義系統,雨傘在功能意義上的覆蓋與顏料在物質上的覆蓋塗抹。
另外,在當代環境充斥的攝影影像也被納進於璽安的創作當中,這些作品彷彿描繪一件件已裱褙的照片。我們可以聯想到攝影在生活中片段取景的框取與繪畫的構圖在脈絡上的連結,較為複雜的是它不只是單張照片,而是連外框中的裱褙空間也一同畫進去,通常照片外圍底襯的留白是作為安置畫面的呼吸空間,而璽安的作品並非留白,而是一種由暗底經重複層疊而顯現的淺色,使得他的作品變成新的繪畫構成空間。唯有讓人困惑的是,攝影影像在當代的特性,即所傳達的語意於當代環境的變化,在璽安的作品裡似乎被擱置。攝影的使用常與記憶(個人性)或事件(社會性)相關,但璽安在挑選攝影影像的內容中則迴避這兩種的使用。對於內容的選擇,他說:「這些作品的內容都為了一種更開闊的空間而生」。作品吸引觀者踏上一個未知的旅程,透過大塊的色面、淡化主題與背景的空間、不同傳達意義的對照思索,引發一種新的想像空間。璽安繪畫中的風景時常是無人的景象,顯現一種孤寂的感受,不禁讓人想問在擁擠狹窄的都市環境,為何選擇創作一種視野更遼闊的作品?面對夕陽時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科學上的解釋(例如地球的旋轉使太陽從地球的西邊落下),另一種是難以言喻個人直觀式的感受,一種純粹直觀的時空觀念,然而我們對現實的理解逐漸轉變為技術化、功能化與媒體界面景觀世界。璽安並不關心於片段生滅,瞬息即逝的事物,反而關心一種恆在的象徵意義,那是透過個人才能揭露與感知,無法用語言明說的,這也說明了圖像的意義不僅僅是像「文字」的智識理解或「事物」的功能意義,璽安說:「當我意識到那個複雜而幾乎無法討論的外在世界時,那個外在世界也就等於是一個空無的意義,但也因為這個空無意義多半也是語言之外的,所以藝術的形式特徵便是珍貴的,因為這個形式或可觸進那些我們說不出的空無」。
[1] 王璽安 著(2006)。《段落的景物與繪畫形式的關係:繪畫性實踐創作與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