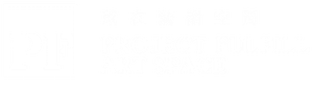盒子上的星空
文╱黃建宏 (刊於 今藝術 2011 11月號)
當我們注視畫面中細微彷如塵埃或星星的亮點時,
會發現它們其實是人形、鳥、葉子或花瓣,
而且
從一疊疊的圖層下浮凸出來,有著圖樣雕琢般的堅實感,
優雅卻無性地脫離我們對於底色的任何想像。
浮留在底圖上的痕跡就是這些亮點之間的細微間隔,和這些間隔之間形成的動態:脫離又閃動。這些實體亮點並不是來自創作者意識中預先存在的命令,或被標示在頒布這命令背後任何藝術意志的底稿上,而是意象流變與繪畫過程之間的對話,這取代了底稿的對話,讓「星叢」在畫面上造成的碎雜位差和關係的薄弱感,與亮點的實體感之間形成一種莫名的深度:圓實與纖薄、形象與關係兩端不同質性間的差距所拉出的深度。
星星與星距,這並非來自「蘊含」而是出自「落差」的深度,可以說是王璽安在不打底稿的畫面上所進行的精確處理。甚至更進一步地,或許為了標示出繪畫的現實感,也或許因為某種極端性格,他用滴流與平刷的薄層,以及與厚厚的層疊底色形成對比而浮出畫布表面的「薄片」,這稀薄的表面與疊色過程的時空,不僅呈現出時空異質的狀態,而且也在兩個時空之間鑿啄出許多蟲洞。這個對比與差距就是由繪畫行為和意象流變來加以縫補和穿透。
被壓印在影子、花瓣和羽毛上的墜落感
稀薄與層積之間的縫補,首先就是為了將繪畫變換為具有反思與批判性的行為,創構出一種人類學式的行為;
再則,台灣的渾變經驗不就是從一層層稀薄的時間積層中,緩慢地浮澱出一顆顆細微而無法預先決定的實體,以及在遠離藝術意志下──因為這意志不是羅伊斯•里戈的無人稱藝術,而是文化殖民下的政治幻見──對於未來之能動的想望,由脆弱而纖薄的星叢關係所形成的想望;然而,這種帶著曖昧、欲望與死亡的深度,在藝術家的各種繪畫展現中,總是相對著觀者的視網膜,由疊層不斷地往上頂,但在高張的表面上,卻又讓我們看見顏色在層疊隙縫中的零碎痕跡,脆弱地彷彿得以窺見浮冰下──曾經充滿欲望的屍體。
這使得王璽安的「畫面」相較於繪畫而言,更像影像,更像貼在身體上的薄紗,而這身體,就是在台灣進行繪畫的身體:沒有完整歷史的史詩性身體
如此,影像時代中的繪畫,就藝術家的台灣經驗,就藝術家在旅行中的異國所見,變成了一種反投影與反成像的「行為藝術」,但這個「反」最矛盾的就是並非影像與身體的對質,而是在身體與圖像、顏色、線條的交叉轉譯中,完成一種介於淺浮雕、影像和認知之間的「行為-物件」。
可以與「行為-物件」相對應的已知經驗,應該是器物圖飾和壁畫的繪製,也就是影像與物理世界的結合,因此,它既非投影也不是成像的自主與自足影像,而是黏合。當然,王璽安的黏合比一般想像的黏合更為複雜,而這個「更為複雜」無論是沉重的心理糾結或是虛擬的美學拓樸,都是「渾變」(trans-plex)的創造性癥候。
於是,我們甚至可以假設這樣的繪畫是一種行為的策畫和實踐,當然
也同時完成著關於物料黏著的各種抽象想像。
在「行為-物件」的策劃與實踐中,
1)知識與議題不再因為歸順於藝術與社會間的倫理次序,進而要求藝術作為再現手段,而相對地作為「行為-物件」的劇本和設定。
2)繪畫的過程因為融合著脈絡意義和媒材意義,成為一種藝術對話關係的建模行為,甚至可以說是建模行為的設計與示範。
3)當物料呈現與承受的是黏合的過程,它就脫離了充分表達情感與象徵意念的角色,而是作為被操作的有機物,進入影像化的劇烈過程。
繪畫脫離牆面的可能性之一,或許可以成立於藝術家建立起他和世界的對話關係之時,也因此,繪畫或許真的需要王璽安所說的「人類學式的考察」和社會行為,才可能改變繪畫的位置。當然,普普、表面支架、照像寫實和超前衛讓圖像和形象在畫面上形成影像的雙重性與弔詭性,而新繪畫則在另一方面讓筆觸的當下性更為直白地入侵圖面,或是讓畫作成為記錄生命史與社會關係的見證式物件,它們都提示出繪畫的「會話」潛能;也因此,繪畫從美術館的史詩性和肖像式崇高轉化為今天雙年展與文件展中的部分物件(甚至可想作「小對體」)。
然而,王璽安作品中出現的天台上的類星空,或許不只是將繪畫影像策略性地當作第三世界藝術家被當代藝術之眼期待的小對體,而是以一種繪畫演出──類似性別演出──的「行為-物件」將繪畫變成為劇場:一種成為慾望機器的幻見劇場。天台上的星空自身就是盒子,盒子上的星空就是反投射的黏合,但「黏合」或許不是追求快感的行為,而是一種結晶般的哀愁。
會發現它們其實是人形、鳥、葉子或花瓣,
而且
從一疊疊的圖層下浮凸出來,有著圖樣雕琢般的堅實感,
優雅卻無性地脫離我們對於底色的任何想像。
浮留在底圖上的痕跡就是這些亮點之間的細微間隔,和這些間隔之間形成的動態:脫離又閃動。這些實體亮點並不是來自創作者意識中預先存在的命令,或被標示在頒布這命令背後任何藝術意志的底稿上,而是意象流變與繪畫過程之間的對話,這取代了底稿的對話,讓「星叢」在畫面上造成的碎雜位差和關係的薄弱感,與亮點的實體感之間形成一種莫名的深度:圓實與纖薄、形象與關係兩端不同質性間的差距所拉出的深度。
星星與星距,這並非來自「蘊含」而是出自「落差」的深度,可以說是王璽安在不打底稿的畫面上所進行的精確處理。甚至更進一步地,或許為了標示出繪畫的現實感,也或許因為某種極端性格,他用滴流與平刷的薄層,以及與厚厚的層疊底色形成對比而浮出畫布表面的「薄片」,這稀薄的表面與疊色過程的時空,不僅呈現出時空異質的狀態,而且也在兩個時空之間鑿啄出許多蟲洞。這個對比與差距就是由繪畫行為和意象流變來加以縫補和穿透。
被壓印在影子、花瓣和羽毛上的墜落感
稀薄與層積之間的縫補,首先就是為了將繪畫變換為具有反思與批判性的行為,創構出一種人類學式的行為;
再則,台灣的渾變經驗不就是從一層層稀薄的時間積層中,緩慢地浮澱出一顆顆細微而無法預先決定的實體,以及在遠離藝術意志下──因為這意志不是羅伊斯•里戈的無人稱藝術,而是文化殖民下的政治幻見──對於未來之能動的想望,由脆弱而纖薄的星叢關係所形成的想望;然而,這種帶著曖昧、欲望與死亡的深度,在藝術家的各種繪畫展現中,總是相對著觀者的視網膜,由疊層不斷地往上頂,但在高張的表面上,卻又讓我們看見顏色在層疊隙縫中的零碎痕跡,脆弱地彷彿得以窺見浮冰下──曾經充滿欲望的屍體。
這使得王璽安的「畫面」相較於繪畫而言,更像影像,更像貼在身體上的薄紗,而這身體,就是在台灣進行繪畫的身體:沒有完整歷史的史詩性身體
如此,影像時代中的繪畫,就藝術家的台灣經驗,就藝術家在旅行中的異國所見,變成了一種反投影與反成像的「行為藝術」,但這個「反」最矛盾的就是並非影像與身體的對質,而是在身體與圖像、顏色、線條的交叉轉譯中,完成一種介於淺浮雕、影像和認知之間的「行為-物件」。
可以與「行為-物件」相對應的已知經驗,應該是器物圖飾和壁畫的繪製,也就是影像與物理世界的結合,因此,它既非投影也不是成像的自主與自足影像,而是黏合。當然,王璽安的黏合比一般想像的黏合更為複雜,而這個「更為複雜」無論是沉重的心理糾結或是虛擬的美學拓樸,都是「渾變」(trans-plex)的創造性癥候。
於是,我們甚至可以假設這樣的繪畫是一種行為的策畫和實踐,當然
也同時完成著關於物料黏著的各種抽象想像。
在「行為-物件」的策劃與實踐中,
1)知識與議題不再因為歸順於藝術與社會間的倫理次序,進而要求藝術作為再現手段,而相對地作為「行為-物件」的劇本和設定。
2)繪畫的過程因為融合著脈絡意義和媒材意義,成為一種藝術對話關係的建模行為,甚至可以說是建模行為的設計與示範。
3)當物料呈現與承受的是黏合的過程,它就脫離了充分表達情感與象徵意念的角色,而是作為被操作的有機物,進入影像化的劇烈過程。
繪畫脫離牆面的可能性之一,或許可以成立於藝術家建立起他和世界的對話關係之時,也因此,繪畫或許真的需要王璽安所說的「人類學式的考察」和社會行為,才可能改變繪畫的位置。當然,普普、表面支架、照像寫實和超前衛讓圖像和形象在畫面上形成影像的雙重性與弔詭性,而新繪畫則在另一方面讓筆觸的當下性更為直白地入侵圖面,或是讓畫作成為記錄生命史與社會關係的見證式物件,它們都提示出繪畫的「會話」潛能;也因此,繪畫從美術館的史詩性和肖像式崇高轉化為今天雙年展與文件展中的部分物件(甚至可想作「小對體」)。
然而,王璽安作品中出現的天台上的類星空,或許不只是將繪畫影像策略性地當作第三世界藝術家被當代藝術之眼期待的小對體,而是以一種繪畫演出──類似性別演出──的「行為-物件」將繪畫變成為劇場:一種成為慾望機器的幻見劇場。天台上的星空自身就是盒子,盒子上的星空就是反投射的黏合,但「黏合」或許不是追求快感的行為,而是一種結晶般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