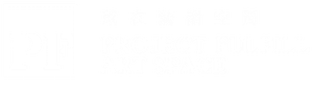廢廟中不斷反覆的可疑可怕儀式─寫張徐展於就在藝術空間中的個展《SI SO MI》
文/黃海鳴
摘要:
這裡並不想透過張徐展的精彩創作去處理傳統民間宗教元素與台灣當代藝術結合的技術性問題,特別是台灣當代藝術應該盡量結合傳統民間宗教內涵的一般性的、理論性的探討。而是觀察運用最有利的各種元素去訴說更容易了解、更容易產生共鳴的一個新的寓言故事,它所指涉的真實故事現在當然還有,過去也早就存在,並且經常發生。在到處都充斥著轉型正義的行動以及討論的當下,我認為這個展覽和這個大潮流有相當關係,但從一個稍微抽離以及文化批判的位置。
這是從一隻被踩扁的小老鼠以及另一隻水桶中掙扎最後也死掉的老鼠開始所發展的一齣黑色鬧劇,它非常容易進入卻一點也不簡單,因為它是關於一隻可愛的老鼠在一個可疑的地方的一個可疑的儀式中被莫名其妙地犧牲,並且連執行儀式的一群人也一起犧牲的故事。它並非偶然發生,而是過一段時間就會再發生一次的儀式。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就會透過殺戮替死鬼的方式讓社會重歸平靜。
藝術家張徐展結合紙雕製作的荒郊野外的奇怪寺廟場景、喪儀中常見的靈厝紙紮藝術,以及被複雜地轉化的SI SO MI喪禮西樂隊音樂、中西新舊俗聖混和的歌舞表演等等所製作的非常精緻的紙紮動畫電影,非常詭譎靈異也讓人覺得熟悉容易共鳴,但不能只停在這個熟悉的位置。
一、 一個初步的簡單地描述:
看起來有點像一個慶祝小孩子生日的歡樂節慶儀式,影片中有一隻可愛、清純、膽怯的老鼠小孩,牠應該是儀式中的主角,其實不然。其他顯得的衰老、醜陋,骯髒,噁心的一群來參加生日派對的大人老鼠們,聲勢浩大、行為乖張,比較像一些藉機行樂的流浪癩痢狗或甚至是活殭屍。與其說是慶祝生日的派對,幾乎就是台灣傳統的喪葬儀式的誇張醜化的版本。當那些帶著生日派對頭飾及道具的SI SO MI葬禮西樂隊樂手及中/西、新/舊、俗/聖等混和歌舞表演者極盡能事的吹奏、狂舞時,各顯得詭異、醜陋甚至是齷齪。在深山暗夜樹林中奇怪的寺廟外面廣場所舉辦的這種非常熱鬧、怪誕的儀式,絕對不是慶生而是慶死。好像是透過極盡熱鬧的死亡儀式才能讓世界重新平靜下來。
那間奇怪的有點像靈骨塔的廟寺中住著大量(先前)去世者的靈魂,這些亡靈就像一條一條非常靈活、白白胖胖的蛆,牠的功能其實就是專門處理死人腐爛的屍體。其中最為詭異也最為關鍵的是,這些大量的蛆以漩渦的形式排列並且旋轉,也許可以看成是典禮中看熱鬧的觀眾,但是更像是以一種匿名、沒有面孔的方式,沒有感覺也沒有罪惡感將可愛的小老鼠淹死,也同時將慶祝生日的醜陋、噁心的大老鼠們,或更像送葬儀式中的樂手、歌舞團員們一起淹死。
我們可以透過紙紮動畫電影中樹幹上以玻璃紙表現的水痕,知道大水掩沒了整個樹林以及這些老鼠樂手、老鼠歌舞團員們。剛開始牠們完全不知死活地賣命表演,甚至把自己肚子裡流出來的腸子當裝飾、道具拼命盡其能事的演出。接著牠們的姿勢越來越像是在水中拼命無望地掙扎直到滅頂的狀態。
總之,在這個奇怪的儀式中,活的年輕的老鼠被某種集體的共識所淹死,當然活的年輕的老鼠就變成了一隻死老鼠,接著來慶祝生日派對的樂團、歌舞團變成了葬儀中的SI SO MI 西樂隊、葬禮特有的歌舞團。也許這個老鼠歌舞團在模擬其他老鼠死前的慘狀。
我覺得這些葬禮老鼠樂隊、葬禮老鼠歌舞團最後也被同樣的水淹死。而最後,沒有面孔、成漩渦裝排列的蛆,將新的死者的屍體、送葬樂團、歌舞團團員的屍體等都完全處理乾淨之後,像是進行某種例行公事,從林中小廣場快速悄悄退回到荒郊野外一間奇怪的寺廟的內部,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段安靜的時間之後,電影又開始重播,同樣詭異的故事再重演一遍。
二、斗膽的詮釋發展及修正過程:
這部動畫電影所牽涉的當然不是慶祝生日的儀式,也不是一種簡單葬禮的儀式,開始時是有點像生日派對的節慶儀式,然後馬上轉變為一種怪異的葬禮儀式。這個可愛的小老鼠的葬禮又為何表現得如此狂歡?直接執行葬禮儀式的隊伍為何被處理得如此齷齪?以及那個可疑的、匿名的、沒有面孔、像蛆一樣的有生命體又是誰?牠們的功能似乎最後把新的死者--犧牲者,以及執行送葬儀式的隊伍都一起殺死、淹死,並且在消滅所有痕跡之後,很有經驗地、不帶情緒地,退回到某種機構內部,好像從此銷聲匿跡。
當然用老鼠的形象來演出是有趣的、有利的,小老鼠或許可愛,老鼠總是和偷竊、破壞以及傳染致命的疾病等連結在一起,牠們本來就是鼠輩嘛!接著,我想到了這會不會和某種獻祭儀式有關連?通常出現某種嚴重破壞父權或國族社會秩序因而引起危機感時,經常會出現獻祭儀式,它是一種為解除危機所需要設立的機制。假如,這是一種獻祭的儀式,那些執行生日派對或葬禮儀式的那些醜陋甚至齷齪的老老鼠,以及那一群匿名、沒有面孔的蛆等,應該都是執行這獻祭儀式的必要的外圍的配備。
真正主腦者應該藏在奇怪的大廟之中,真正的主腦一般不會以這種醜陋的形象出現。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那個真正促成獻祭儀式的很可能就是那個匿名、沒有面孔的大眾,主腦人只是善用時機,運用他們的無知、盲從、衝動來行使它想做的事情。這樣的詮釋似乎有一點道理,但未免過度簡單。
有沒有可能那隻天真的老鼠在一個時代轉變的時候做了一些有開創性的事情,並且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並且熱烈支持,於是瞬間變成為一位年輕英雄意見領袖,但是當其行為言語超過一定界線,原先同意的人可能在某些引導下快速反過來變成指責這位造次者已經破壞了既有秩序。年輕英雄突然變成傳染致命病毒的該死者。這樣,原來贊同者也轉變為殘忍的判罪者。
因此,這些先前群起表白贊同,接著又群起歸罪的這些老鼠們,被使用最難看的形象來處理。我認為這裡更難看的形象還不是這些又老又醜又齷齪的鼠輩,而是那一群匿名的、沒有面孔的,慶祝的時候可以一起慶祝,情勢改變後,指責歸罪的的嘴臉比誰都要兇狠,甚至圍觀死刑儀式中也能夠情緒亢奮,但是不管怎麼樣牠們都是匿名的、沒有面孔的,完全不需要負責,也沒有任何罪惡感。可是那些直接參與儀式的社群,不管是主動或其身分不得不,就難免要承擔各種衝突矛盾,甚至最後也要承擔曾經殺死英雄的沉重代價。
那一大群跟在四周附和像蛆一樣的生命體又是誰?他們匆匆忙忙地跟隨、 看熱鬧,也匆匆忙忙地處理被犧牲者的屍體,然後讓所有的痕跡煙消雲散,好像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然後等待下一次的類似的儀式?製作非常精細的紙紮寺廟,破廟門口裡面的那面鏡子是要那些生命反身照照自己曾經做過哪些殘忍又不負責的事情?顯然包括所有的觀賞者都想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就像那隻被踩遍的老鼠,牠的旁邊就放了一面巨大的鏡子,面對這面鏡子牠要思考為何牠要趟在這裡?是因為牠犯了罪?是因為牠一出生就有罪?不管做對做錯,是因為牠的某些行為已經被當成社會不安全的原因?牠的犧牲可以幫助特定部落解除危機而重新獲得秩序?以及有多少人迷迷糊糊附和這樣的集體共識,相互形成一種巨大的催眠力量,讓加害者們理所當然地一起去促成這種殺戮而不需承擔任何罪惡,甚至連犧牲者也同意?從這個展覽中的許多條件,似乎可以讓我們往這個方想思考,我們是不是偶爾也變成那些讓不正義的事情發生,又不需負責也沒有罪惡感的匿名者、沒有面孔的人?
三、賤斥體的普遍結構,與周而復始的殺戮替罪羊的儀式:
現在可以從細節中退出,綜觀整部錄像電影都有一種汙穢、骯髒,病毒、低下、落伍的感覺。傳染鼠疫的老鼠可以被放在這個脈絡,像流浪癩痢狗一樣衰老生病老鼠當然更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那麼人呢?哪一類的人會被放在這樣的脈落?那麼文化呢?哪一類的文化會被放在這樣的脈絡?在現代藝術的脈絡中,在很長的時間和民間宗教有關的文化藝術被放在這樣的脈絡中。那些和民間宗教中直接和死亡或死亡儀式有關的文化藝術形式,更被放在這樣的脈絡,並且很難翻身,那麼某些聲音、某些感性、 某些世界觀等,不就沒有機會被聽到?在回到這段的脈絡,那麼,直接執行和民間宗教死亡儀式有關的人、職業社群等是不是也被放在這樣的脈絡?
就直接一點吧!家裡經營紙紮行業的人會不會有這樣的困擾?和民間宗教定義下的死亡有密切關係的各種行業的人,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困擾?他們是社會的必要,還包含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必要,但卻必須承擔這樣的避之惟恐不及的汙穢感?當然這件作品讓我聯想到克莉斯蒂娃所提的「賤斥」的問題。被定義為賤斥的物質或性質,一般都具有很強的「邊界性格」,座落於生/死、男/女、乾淨/汙穢、神聖/褻瀆等等的界線之間,它們的存在重新喚醒主體們對於陰性空間的記憶,回到「人尚未成人」,一切尚未被清楚劃分的太初混沌中。張徐展所創作的相關藝術表現中,像這一類的「未被清楚劃界」的狀態是非常明顯的。
我想藝術家對於被視為賤斥體的自覺一定是有的,我想問的是,在他這次的作品中它是主要的部份?還是次要的部分?或一向可以從這裡開始當作基礎去滲透拓展其他層面的思考以及表現?例如在社會中仍然持續進行的某種遠古時期,人們以牲畜獻祭,透過獻祭的各種儀式,以他者的鮮血,換取自我的安寧。而更瘋狂的,就指認他人為女巫,將罪惡的符號與之等同。人們獵殺女巫,施以火刑,就這樣牲畜與巫者,從而成了集體暴力下的「替罪羊」。
這些儀式興起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恐懼,並且恐懼著「恐懼」。多半的時刻,人們需要安寧,對於不確定的神祕事物,對於自身內部的可能投影,總想要驅逐,於是,藉由殺戮「替罪羊」的儀式,罪惡與不確定彷彿就不再存在,使自我得到暫時的滌淨。當然,張徐展的作品總是包含了許多因為家族所經營的行業而非常不一樣的直接的經驗組合。這些寶貴的親身經驗,以及熟悉可用的符號,也非常有利於深刻的宏觀的人類學的思考以及延伸的藝術表現。
四、結語:並置的另一種觀看或自省的方式:
張徐展一人包辦全部製作的紙紮藝術動畫電影,除了他本人必須進入所有角色身體以及內心,也必須能綜觀角色之間的複雜糾結關係。另一方面他的創作可以直接提供觀賞者兩種的藝術呈現:一種用電影的方式,張徐展引導了觀眾的眼睛;一次是用劇場裝置藝術的方式,張徐展還給觀眾自由的觀賞或凝視的角度以及路線。不管哪一種都給人非常貼近、生動的感覺。
在動畫電影的方面,誇張醜陋又非常自得的動作就在我們面前毫不羞愧地演出,任何的生活實境或是藝術表演我們都不可能靠得那麼近觀賞,特別是近到可以讓人看得到他們的嘴巴、喉嚨、眼皮、眼珠、皺紋、甚至是連會隨著身體擺動或隨著呼吸而擺動、震動的鬍鬚也看得清清楚楚。說簡單點,表演者完全看不到我們,我們卻能看見以及直接感受到表演者身體上一切的細節改變,好像我們就是這些通常演給鬼神看的戲的無形觀賞者,我們就是鬼神或者是亡靈。
我們在這個地方被賦予某種全知的角度,特別是我們的腳步轉到黑暗房間中那個非常精細的全景舞台,比我們的眼睛視線還要低的非常精細的全景舞台。我們可以相當自由自在地從各種靜態的、動態的角度、距離觀看、思索,那些立體的造型並非全然像蠟像館的蠟像,因為他們就是本尊,曾經動過、幾分鐘之前還非常生動地動過,有靈魂住在其中、或暫住其中。
裝置劇場實景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放著一隻被壓扁的小老鼠,還不斷自問牠為何要被壓扁、棄置於此,無人收屍,或許無人敢收屍?那座奇怪的寺廟的入口處也設了一片鏡子,也許要問所有觀賞者的問題是:在這個經常重演的恐怖儀式中我們自覺或不自覺擔任了哪一個角色?
這樣的並置,在動靜交替之間,非常有助於神入創作者內心,神入各種角色內心。這件創作,這個有關葬禮紙紮老鼠社群的寓言故事,不是要回到歷史,而是要借用歷史,要面對當下的社會困境或是困難的轉型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