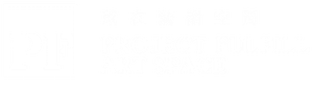The Tendency to a New Factor in Human Condition
邁向一個新人類狀態的趨勢
文╱ 王焜生 Emerson Wang
建築素描或工業機械繪圖似的繪畫多年來幾乎成為陳建榮作品的標誌。觀者或評論家經常將他的繪畫與建築或機械並列談論,指涉出現代文明的工業現象、秩序性的城市與極為理性的觀照視野。
但是熟悉藝術家的朋友或許會有不同的認識,他的溫文像是刻意拉出的冷眼旁觀距離,就如同他的作品一般,情感隱而未見,抑或只是在簡單的線條與色彩之間才能透漏出些許溫暖端倪;又或者是只有當他在球場上揮汗如雨,與隊友之間的運球傳遞之間才能看到他不同於畫布上的剽悍與豪邁。
建築學(architectonic)狹義上所要研究的是建築物所環繞的使用空間、產生的形象,以及衍伸出被欣賞的美學層次問題;廣義上而言,建築學所關注的不僅是建築物本身與空間,更核心的焦點是在人類與建構物的交互關係、人在其空間中的定位以及從設計到完成、從無到有的過程裡人類的心理與身體的滿足狀態。如果以此來看陳建榮的創作,就可以清楚發現他的畫面構成實則藉機械營造的理性繪圖過程來處理他對某種“秩序性”的執著與偏好。
再仔細端詳藝術家的作品,之前一直被認為是具有結構性的建築或機械素描,其實卻存在一種非常不真實的情狀。它們不具建築與工業器材的標準尺規比例以及得以成為實際製作成物的條件,原本繪畫表面所呈現的秩序與規則一夕之間突然成為抽象的概念,觀者誤以為的理性刻度轉而成為極為內在的私密風景。每一筆線條、每一個刻度、每一個直角、每一個像是機械零件的圖像都成為感知的度量衡。下筆的剎那都有藝術家尋找情緒抒發的快感,這個移情作用也透露出陳建榮面對創作的態度與心情:嚴肅而戰戰兢兢。每件作品他都期望是沒有後悔的,斟酌再三才下筆,之後又必須一再端詳審視,一再修改。
藝術的諸多任務之一是對社會或一般價值的支配理念與虔誠地位提出質疑,並且做出抗辯。即使不在對抗的時候或當下,也是朝著反對的方向前進,這是藝術家天生的反骨也是無法捨棄的宿命。陳建榮的Landscape 捨棄許多自然的元素,潛心建構屬於“人為風景”的範疇。從語源學(etymology)的角度來看,拉丁及日耳曼語系(German Language)所指稱的“風景”一詞從語源學(etymology)的發展研究上看出其語意隨着時代的改變而有所差異,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差異,在地理學與藝術學上的指涉也不盡相同,文學上所解釋的更直接說明是自然的景色;英語landscape的德文為 Landschaft,更能指出這個字的源流意涵,schaft指的是關係的意思,亦就是自然與之對應的關係組成為文句上的風景意涵。大地還需包涵創造(creation)、對象(creature)、組成成分(constitution)、與狀態情境(condition)才能成為「風景 」。
風景地理學者歐維格(Kenneth Olwig)2002年的著作《風景、自然與身體政治》(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以及《自然的意識形態風景》(Nature’s Ideological Landscape, 1984 )都主張對風景與環境進行實質的關注滲過於單純藝術學理上的言說。此也意味著,所謂的風景畫對當代藝術家而言不在只是自然形象地描繪,中間夾雜了藝術家對環境的感知,以及政治學上的全力對抗。
陳建榮的風景系列所處理的,當然也跳脫了單純形象與景觀的描繪,這個風景毋寧是藝術家在身處環境下對自然的論述,如建築物的藍圖線條與構築草案成為當下現實的寫照。
認知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基模 (schema),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理論中的基本觀念之一,以基模來解釋個體如何認識並適應環境的知識表徵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當一個人面臨刺激情境或問題情境時,會先以既有的認知架構作為核對方式,產生認知作用,將所遇到的新經驗,納入其舊有經驗的架構內成為同化(assimilation)。
陳建榮的創作過程中許多的呈現方式也持續回應著童年的經驗與記憶,從實際的雙手接觸操作材質不同、形象各異的機器人,甚至是每個零件的解構與重組拼裝都成為他心靈裡極為個人化的觀看世界模式。機器人是個機械所繪製製造出的虛擬形象,卻又能成為人類的某方面替代,在拆解與組裝過程裡像是進行一個新人類世的發現,其中包涵的是人為可以決定的機械性以及像人類無法掌握性。這個雙面性的矛盾確實也存在當今的社會,陳建榮的作品呈現了藝術家從生活經驗到自我設想的宇宙裡。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將理性當作獲得“自生的知識”(selbsterkenntis)的前提,強調一個獨立實體不經過“權威的信條”(despotic decrees)卻能依靠永恆的、不變的自在法則實現正確審視的能力。即使求學時期,從大學到研究所,每一位老師都給了陳建榮各種面向的藝術養分,特別是在技巧與對繪畫問題的解決上,但是依據每位藝術家心性氣質的差異,呈現出來的創作自然有極大的差異。因此,觀看陳建榮的作品也必須回歸到一位藝術家對創作的信念上,而不是僅在技巧與表面的形象上試圖形塑出他的輪廓。陳建榮的內在有一個自我建構的理性系統,從而引領他的創作走向在理性的表徵裡隱喻感性的幽微。
康德認為的認識論也植基於如同建築學的系統上,從人類先驗性的直覺逐漸整合出系統化的邏輯性知識架構,從純粹的理解範疇(或稱為比較感性的內在)框架出如建築方式的基模,再逐漸轉化為一個審美的標準。當觀看陳建榮的作品時,我倒是比較以這樣的方式來逐步拆解他創作的內涵,也就是他對藝術呈現上認知的態度與觀察。“建築架構”成為接近陳建榮作品的第一道橋粱,但是觀眾必須跨過去並且走進他的世界才能體會到作品形象之外的情感。
人們通過「時間」與「空間」形式獲得的感性認識並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認識直觀材料,但要透過更高一層被稱為「知性」的人類思維活動概念才能進行判斷推理的思維能力。康德說:「思維無內容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的。」兩者組織後才能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知識。而我認為在陳建榮的作品中即使他呈現的是節制的理性,但是內在卻還是有許多東方哲思的感性在裡面。「現象界」中的物質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無法滿足人類的求知慾望,人們運用「先天的」思維形式對這一過程混亂零散的感覺材料進行整理加工後,人們才能獲得感性的認識。只有從人類的立場,才能談到空間與時間,它們不可能離開人類主體而獨立存在,它們屬於人類的條件,同時也是人類感知的先天方式。
陳建榮類建築藍圖式的繪畫讓我聯想到德國建築師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於1929年 在西班牙巴塞隆納世界博覽會所設計的德國國家館。一棟臨時的建築本來應當在展覽結束後就拆除,所以展覽館並沒有實質的外牆,四周全部由大片的玻璃構成,平坦的屋頂僅由細長而風格化的鋼架支撐,給觀眾的感覺是靜謐且井然有序,建築物裡面除了他自己設計的傢俱外別無他物,建築物外唯一的一件雕塑是科爾貝(Georg Kolbe)的等身裸女。這是一件對於方角型單純結構的禮讚,裸女雕像是唯一俱有曲線的形體。最後這棟建築被保留下來,我們得以再次體會複雜但和諧的整體。
現代建築主義有兩個特色:「忠實」(honesty)與「簡約」(simplicity),但是反而成為前衛建築師用以撻伐墨守成規的同行。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曾說:「某些簡單的形式和處理方式可以突出木頭的美,而另一些形式則無法做到。」對於過多的木雕裝飾物,萊特都認為太俗氣並且過於精雕細琢,隱含的是建築師必須要有睿智使用機械,讓機器臣服於建築師的目的。除了忠實與簡約之外,萊特也即為信仰「有機 」(organic),也就是保持內外元素完全一致的和諧。當然,觀看陳建榮的作品不應等同於觀看建築師的計劃藍圖,或是想象即將被實現的可能,卻在其中富含藝術家內在自我構築的一方世界。機械玩具的每一個組合所顯示的精準與單純,加上如同建築繪畫的語彙,恰恰回應了藝術家的個性,也清楚而無阻礙的呈現在他的作品中。
幾何圖形是最被容易理解的形式,顏色也包含在形式裡,沒有了色彩,形式也會消失,即便是低限度的色系都還是強烈的表現出光譜的視覺效應。從陳建榮的作品中恰好看到這兩個最基本元素的單純呈現,幾何圖形與光譜色彩,恰如其分的扮演言說藝術創作在藝術家作品裡的重要角色。
德國包浩斯藝術學院(Bauhaus)在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與伊登(Johannes Itten)執教時更重視色彩為基礎設計的重要課程,特別是伊登的「基本色彩理論」(Zur Farbenlehre)與之後發展的「伊登色環」(Farbkreis)至今都被廣泛使用。伊登認為感情狀態能透過色彩與形式傳達出來;康丁斯基延續自歌德到人類學家史代納(Rudolf Steiner)關於色彩的理論,提出「色溫」(Farbtemperatur)在圖像的地位,當然他所提出的點、現、面法則與整理構圖理論至今都還影響藝術學院的教學甚深。
陳建榮作品中除了線條與畫面的建構之外,色彩也是一個精彩而值得探究的元素。他以冷調的色系凸顯形象的辨識,減少過多跳躍的淺白視覺意象,然而最近的新作中,他也嘗試運用一些看似更為人工化的色調來呈現眼睛所見所感的世界。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於2003年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所頒發的年度德國書商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時發表演說,其中一段話:「文學是對話,是回應。文學也許可被描述為人類隨著各種文化的演變和彼此互動而對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將消失的事物作出回應的歷史」。藝術,當可也作如觀。
「Landscape」與「Aircraft 」是陳建榮近年創作的兩個主軸。從觀眾熟悉的建築物逐漸拉開場景到建築物與環境;從手邊可以取得的玩具到超乎日常生活的大型航空機械,同樣的「人」的形象在他作品中仍然是表面上的缺席,但卻又無所不在。
反覆觀看陳建榮的每一件畫作,突然讓我掉入2005年參觀第九屆土耳其伊斯坦堡雙年展(The 9th Istanbul Biennial)的回憶裡。該年的展覽標題簡單明暸的直接為《伊斯坦堡》,之前讀過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筆下一個冷眼旁觀的土耳其人描述他的故鄉,一個曾經叱咤歷史的奧圖曼的帝國輝煌與今日的頹圮墮落形成人類歷史的冷酷,同時顯露了傳統與現代之間衝突的感傷,這個風景不是眼前所見而已,她還包含了幾千年累積下來的人類文明史。當年的雙年展,我們依著導覽指標在城市之間遊走,最繁華熱鬧的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Meydani)與大街,曾經經歷暴動,如今二十四小時的青少年文化橫流,對照荷槍實彈的警察,在在充滿衝突;然後走過髒亂廢棄的巷弄,在每一棟無人居住的破舊物屋舍裡觀看當代藝術家回應此處歷史的作品。那也是一種風景,一種看不見人卻處處充滿人的歷史的風景。
「是凝固的音樂」為陳建榮2014年展覽的標題,開放了一個讓觀者自由映照的關係。
標題源自於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803年在他的著作《藝術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Kunst)裡談論建築與音樂的關係時所提到的「建築如同凝固的音樂」(die Architektur als erstarrte Musik),1833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再度於他的《箴言與自省》(Maximen und Reflexionen)中再度援引稱之「沉默的樂音藝術(verstummte Tonkunst),指出建築與音樂之間的和諧與調和關係,甚至到二十世紀仍然有建築師對前人的哲思深表認同。對陳建榮而言,他的作品實際上與建築的關係倒是沒有多大深刻的關聯,但是卻藉由建築結構與機械的形象提示出一個藝術家內在的世界,如同音樂的旋律一般,綿延出個人的心象風景。
但是熟悉藝術家的朋友或許會有不同的認識,他的溫文像是刻意拉出的冷眼旁觀距離,就如同他的作品一般,情感隱而未見,抑或只是在簡單的線條與色彩之間才能透漏出些許溫暖端倪;又或者是只有當他在球場上揮汗如雨,與隊友之間的運球傳遞之間才能看到他不同於畫布上的剽悍與豪邁。
建築學(architectonic)狹義上所要研究的是建築物所環繞的使用空間、產生的形象,以及衍伸出被欣賞的美學層次問題;廣義上而言,建築學所關注的不僅是建築物本身與空間,更核心的焦點是在人類與建構物的交互關係、人在其空間中的定位以及從設計到完成、從無到有的過程裡人類的心理與身體的滿足狀態。如果以此來看陳建榮的創作,就可以清楚發現他的畫面構成實則藉機械營造的理性繪圖過程來處理他對某種“秩序性”的執著與偏好。
再仔細端詳藝術家的作品,之前一直被認為是具有結構性的建築或機械素描,其實卻存在一種非常不真實的情狀。它們不具建築與工業器材的標準尺規比例以及得以成為實際製作成物的條件,原本繪畫表面所呈現的秩序與規則一夕之間突然成為抽象的概念,觀者誤以為的理性刻度轉而成為極為內在的私密風景。每一筆線條、每一個刻度、每一個直角、每一個像是機械零件的圖像都成為感知的度量衡。下筆的剎那都有藝術家尋找情緒抒發的快感,這個移情作用也透露出陳建榮面對創作的態度與心情:嚴肅而戰戰兢兢。每件作品他都期望是沒有後悔的,斟酌再三才下筆,之後又必須一再端詳審視,一再修改。
藝術的諸多任務之一是對社會或一般價值的支配理念與虔誠地位提出質疑,並且做出抗辯。即使不在對抗的時候或當下,也是朝著反對的方向前進,這是藝術家天生的反骨也是無法捨棄的宿命。陳建榮的Landscape 捨棄許多自然的元素,潛心建構屬於“人為風景”的範疇。從語源學(etymology)的角度來看,拉丁及日耳曼語系(German Language)所指稱的“風景”一詞從語源學(etymology)的發展研究上看出其語意隨着時代的改變而有所差異,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差異,在地理學與藝術學上的指涉也不盡相同,文學上所解釋的更直接說明是自然的景色;英語landscape的德文為 Landschaft,更能指出這個字的源流意涵,schaft指的是關係的意思,亦就是自然與之對應的關係組成為文句上的風景意涵。大地還需包涵創造(creation)、對象(creature)、組成成分(constitution)、與狀態情境(condition)才能成為「風景 」。
風景地理學者歐維格(Kenneth Olwig)2002年的著作《風景、自然與身體政治》(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以及《自然的意識形態風景》(Nature’s Ideological Landscape, 1984 )都主張對風景與環境進行實質的關注滲過於單純藝術學理上的言說。此也意味著,所謂的風景畫對當代藝術家而言不在只是自然形象地描繪,中間夾雜了藝術家對環境的感知,以及政治學上的全力對抗。
陳建榮的風景系列所處理的,當然也跳脫了單純形象與景觀的描繪,這個風景毋寧是藝術家在身處環境下對自然的論述,如建築物的藍圖線條與構築草案成為當下現實的寫照。
認知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稱為基模 (schema),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理論中的基本觀念之一,以基模來解釋個體如何認識並適應環境的知識表徵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當一個人面臨刺激情境或問題情境時,會先以既有的認知架構作為核對方式,產生認知作用,將所遇到的新經驗,納入其舊有經驗的架構內成為同化(assimilation)。
陳建榮的創作過程中許多的呈現方式也持續回應著童年的經驗與記憶,從實際的雙手接觸操作材質不同、形象各異的機器人,甚至是每個零件的解構與重組拼裝都成為他心靈裡極為個人化的觀看世界模式。機器人是個機械所繪製製造出的虛擬形象,卻又能成為人類的某方面替代,在拆解與組裝過程裡像是進行一個新人類世的發現,其中包涵的是人為可以決定的機械性以及像人類無法掌握性。這個雙面性的矛盾確實也存在當今的社會,陳建榮的作品呈現了藝術家從生活經驗到自我設想的宇宙裡。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將理性當作獲得“自生的知識”(selbsterkenntis)的前提,強調一個獨立實體不經過“權威的信條”(despotic decrees)卻能依靠永恆的、不變的自在法則實現正確審視的能力。即使求學時期,從大學到研究所,每一位老師都給了陳建榮各種面向的藝術養分,特別是在技巧與對繪畫問題的解決上,但是依據每位藝術家心性氣質的差異,呈現出來的創作自然有極大的差異。因此,觀看陳建榮的作品也必須回歸到一位藝術家對創作的信念上,而不是僅在技巧與表面的形象上試圖形塑出他的輪廓。陳建榮的內在有一個自我建構的理性系統,從而引領他的創作走向在理性的表徵裡隱喻感性的幽微。
康德認為的認識論也植基於如同建築學的系統上,從人類先驗性的直覺逐漸整合出系統化的邏輯性知識架構,從純粹的理解範疇(或稱為比較感性的內在)框架出如建築方式的基模,再逐漸轉化為一個審美的標準。當觀看陳建榮的作品時,我倒是比較以這樣的方式來逐步拆解他創作的內涵,也就是他對藝術呈現上認知的態度與觀察。“建築架構”成為接近陳建榮作品的第一道橋粱,但是觀眾必須跨過去並且走進他的世界才能體會到作品形象之外的情感。
人們通過「時間」與「空間」形式獲得的感性認識並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認識直觀材料,但要透過更高一層被稱為「知性」的人類思維活動概念才能進行判斷推理的思維能力。康德說:「思維無內容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的。」兩者組織後才能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知識。而我認為在陳建榮的作品中即使他呈現的是節制的理性,但是內在卻還是有許多東方哲思的感性在裡面。「現象界」中的物質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無法滿足人類的求知慾望,人們運用「先天的」思維形式對這一過程混亂零散的感覺材料進行整理加工後,人們才能獲得感性的認識。只有從人類的立場,才能談到空間與時間,它們不可能離開人類主體而獨立存在,它們屬於人類的條件,同時也是人類感知的先天方式。
陳建榮類建築藍圖式的繪畫讓我聯想到德國建築師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於1929年 在西班牙巴塞隆納世界博覽會所設計的德國國家館。一棟臨時的建築本來應當在展覽結束後就拆除,所以展覽館並沒有實質的外牆,四周全部由大片的玻璃構成,平坦的屋頂僅由細長而風格化的鋼架支撐,給觀眾的感覺是靜謐且井然有序,建築物裡面除了他自己設計的傢俱外別無他物,建築物外唯一的一件雕塑是科爾貝(Georg Kolbe)的等身裸女。這是一件對於方角型單純結構的禮讚,裸女雕像是唯一俱有曲線的形體。最後這棟建築被保留下來,我們得以再次體會複雜但和諧的整體。
現代建築主義有兩個特色:「忠實」(honesty)與「簡約」(simplicity),但是反而成為前衛建築師用以撻伐墨守成規的同行。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曾說:「某些簡單的形式和處理方式可以突出木頭的美,而另一些形式則無法做到。」對於過多的木雕裝飾物,萊特都認為太俗氣並且過於精雕細琢,隱含的是建築師必須要有睿智使用機械,讓機器臣服於建築師的目的。除了忠實與簡約之外,萊特也即為信仰「有機 」(organic),也就是保持內外元素完全一致的和諧。當然,觀看陳建榮的作品不應等同於觀看建築師的計劃藍圖,或是想象即將被實現的可能,卻在其中富含藝術家內在自我構築的一方世界。機械玩具的每一個組合所顯示的精準與單純,加上如同建築繪畫的語彙,恰恰回應了藝術家的個性,也清楚而無阻礙的呈現在他的作品中。
幾何圖形是最被容易理解的形式,顏色也包含在形式裡,沒有了色彩,形式也會消失,即便是低限度的色系都還是強烈的表現出光譜的視覺效應。從陳建榮的作品中恰好看到這兩個最基本元素的單純呈現,幾何圖形與光譜色彩,恰如其分的扮演言說藝術創作在藝術家作品裡的重要角色。
德國包浩斯藝術學院(Bauhaus)在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與伊登(Johannes Itten)執教時更重視色彩為基礎設計的重要課程,特別是伊登的「基本色彩理論」(Zur Farbenlehre)與之後發展的「伊登色環」(Farbkreis)至今都被廣泛使用。伊登認為感情狀態能透過色彩與形式傳達出來;康丁斯基延續自歌德到人類學家史代納(Rudolf Steiner)關於色彩的理論,提出「色溫」(Farbtemperatur)在圖像的地位,當然他所提出的點、現、面法則與整理構圖理論至今都還影響藝術學院的教學甚深。
陳建榮作品中除了線條與畫面的建構之外,色彩也是一個精彩而值得探究的元素。他以冷調的色系凸顯形象的辨識,減少過多跳躍的淺白視覺意象,然而最近的新作中,他也嘗試運用一些看似更為人工化的色調來呈現眼睛所見所感的世界。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於2003年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所頒發的年度德國書商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時發表演說,其中一段話:「文學是對話,是回應。文學也許可被描述為人類隨著各種文化的演變和彼此互動而對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將消失的事物作出回應的歷史」。藝術,當可也作如觀。
「Landscape」與「Aircraft 」是陳建榮近年創作的兩個主軸。從觀眾熟悉的建築物逐漸拉開場景到建築物與環境;從手邊可以取得的玩具到超乎日常生活的大型航空機械,同樣的「人」的形象在他作品中仍然是表面上的缺席,但卻又無所不在。
反覆觀看陳建榮的每一件畫作,突然讓我掉入2005年參觀第九屆土耳其伊斯坦堡雙年展(The 9th Istanbul Biennial)的回憶裡。該年的展覽標題簡單明暸的直接為《伊斯坦堡》,之前讀過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筆下一個冷眼旁觀的土耳其人描述他的故鄉,一個曾經叱咤歷史的奧圖曼的帝國輝煌與今日的頹圮墮落形成人類歷史的冷酷,同時顯露了傳統與現代之間衝突的感傷,這個風景不是眼前所見而已,她還包含了幾千年累積下來的人類文明史。當年的雙年展,我們依著導覽指標在城市之間遊走,最繁華熱鬧的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Meydani)與大街,曾經經歷暴動,如今二十四小時的青少年文化橫流,對照荷槍實彈的警察,在在充滿衝突;然後走過髒亂廢棄的巷弄,在每一棟無人居住的破舊物屋舍裡觀看當代藝術家回應此處歷史的作品。那也是一種風景,一種看不見人卻處處充滿人的歷史的風景。
「是凝固的音樂」為陳建榮2014年展覽的標題,開放了一個讓觀者自由映照的關係。
標題源自於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803年在他的著作《藝術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Kunst)裡談論建築與音樂的關係時所提到的「建築如同凝固的音樂」(die Architektur als erstarrte Musik),1833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再度於他的《箴言與自省》(Maximen und Reflexionen)中再度援引稱之「沉默的樂音藝術(verstummte Tonkunst),指出建築與音樂之間的和諧與調和關係,甚至到二十世紀仍然有建築師對前人的哲思深表認同。對陳建榮而言,他的作品實際上與建築的關係倒是沒有多大深刻的關聯,但是卻藉由建築結構與機械的形象提示出一個藝術家內在的世界,如同音樂的旋律一般,綿延出個人的心象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