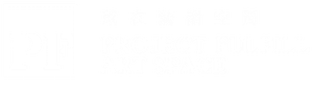Vista
Hsu Ting Solo Exhibition
《遠景》徐婷 個展
Artist talk record 座談記實
與談人:黃建宏(關渡美術館 館長)× 徐婷(藝術家)
與談人:黃建宏(關渡美術館 館長)× 徐婷(藝術家)
徐:這次展覽如果要講創作的發想,可以從我在去年底去台南麻豆、總爺藝文中心去駐村了大概快三個月的時間,那次的駐村經驗帶給我蠻大的衝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台南麻豆,我其實從小一直都是一個生活在城市裡面的人,包括去倫敦都還是一個密度較高的城市的狀態,去麻豆駐村的時候就很深刻的感覺到我是一個很依賴城市生活的人,並很極度地感覺到我其實處在一個很緊繃、不安的狀態。那邊的環境就是很空曠、可以想像,然後也是相對的便利的,所以在駐村的經驗大概是我第一次跳脫了一個比較focus在我內心的情感等等的一個焦點,把我創作的方向去跟外界環境之間的關係的一個經驗。回到台北之後我思考是不是可以去依據我生活的背景-城市生活這個環境,去作為一個對象去描寫。在準備這次的展覽我看到一本書名,它是德國的哲學家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在《時間之書》,裡面的一段文字,那裡面描述了很多不同型態、不同狀態的時間,那其中有一個他描寫到「憂慮的時間」,他說,人好像一直要試圖瞄準什麼東西,這個瞄準是基於在一個緊張的一個狀態,可以在時間上還沒有發生的事情,或是空間上還未到來的一個遠處的一個東西,我就覺得這個瞄準的狀態好像跟我在拍照的時候,拿相機用長鏡頭試圖想要看到遠處的東西的那個狀態,所以就開始有「遠景」的這個展覽想法。我那時候就在思考,人在都市裡面可以看到最遠的畫面是什麼?因為在鄉野、鄉下之間其實房子都很矮,所以你可以看到很遠的畫面,在都市裡面建築的密度都很高,最遠能看到的畫面就是天空的畫面,所以我就選擇了〈Vista-1〉這一件作品去作為展覽開始的一個視覺,由這件作品開端。
黃:如果我們去看待一個創作者,他要表達的是一個他對他的生存環境、他的日常狀態的一個紀錄,或者一種表達,通常在這種作品裡面我們會發現,他其實是在一種比較抽象的距離裡面,去表達一種切身的感覺,那種感覺非常貼近自己的腦袋、或貼近自己的身體感,通常會有這種影像的表達。可是比較難同時間去思考,關於攝影作為一種媒材,或者說作為一種工具的時候,到底我們要如何去思考這樣一個機械建構感情的事情。你的這次展覽叫「遠景」,我覺得這裡面蠻有意思的,這個詞取得很好,因為我們現在攝影的技術、攝影機太多人可以擁有,而且很多人都可以成為行家,也就是說對於這台機器,它的相關的功能,到底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狀態,今天拿起攝影機去進行拍攝,要能夠從裡面去討論「距離」的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大概很多攝影機早就決定了很多照片它拍出來是什麼樣子,人其實是好像在轉角度而已,其他的東西就是這台機器的距離就已經可以測量的,我剛剛為什麼去說另一個極端,人要表達的情緒、他的內在世界抽象的距離。慢慢我們對於一個技術環境的體認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意識到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拿著一台相機,那到底我拍出來的東西如何與別人不同?
現在的攝影會慢慢地去討論這件事,把非常個人的那種內在的距離,它如何可以變成這種對於-為藝術而藝術、對於藝術媒材的反思,能夠讓它有一個關係。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像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攝影,Apichatpong他很多攝影都是跟這他的藝術計畫、還有跟著他的影片拍攝出來的,可是Apichatpong他的攝影到底在追求什麼,那個距離到底是什麼,這也就是在徐婷的作品裡面一個比較有意思而且有價值的地方。很明顯地都可以感受的到,不管是光或者是被截取出來的東西可以猜得出來都來自日常,來自日常的狀態會把它抽象,成為在畫面裡、在空間裡面,因為她的攝影作品的裝置方式,其實非常的強調空間,不直接的依賴牆面,這也是(Wolfgang) Tillmans他用編輯的概念去處理整個攝影跟空間的關係。其實這些東西在台灣都還很少,台灣的攝影如何隨著當代藝術去思考技術跟心靈的距離如何同時被感受到,攝影的影像如何重新回到空間裡面?空間不只是牆面,攝影非常長一段時間,它的空間感其實都在牆面上,可是Tillmans已經做了很大的改變。(就在藝術空間)之前邀請的Dinh Q. Lê(黎光頂),他把攝影用一種長卷的輸出,些東西在台灣的環境裡還很難有系統的、比較有一些積累的方式被討論,這是我很感興趣的地方。我剛為甚麼會舉Apichatpong,他是一個技術能力很強的人,他本身是學實驗電影的,然後又拍電影拍那麼多年,可是他在拍一個東西,或是他在思考那個影像,他的技術跟精神的追求,如何去找到那個平行跟重合的狀態。我覺得在徐婷的創作裡面,其實都顯露出相關的這些可能性。
黃:為何會說到拍攝距離?因為我們很長時間對於攝影的拍攝距離,大部分都還停留在所謂紀實,也就是拿起相機從這個視窗看出去,我跟對象物之間那個距離到底會是什麼,大部分都還是一個寫實的距離。那寫實距離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可能性?十幾年前日本的年輕攝影師就開始在尋找這個東西,很多都必須從微觀,他可能拍一個下過雨的後照鏡,可是洗出來的照片大家會以為他在拍宇宙,就是開始有那種,生命裡面、生活的環境其實越來越貧窮,可是那個夢想其實是越來越烏托邦,在這種狀態裡面的轉換,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發展面向。
徐:我覺得剛剛老師提到其實有關於很多不同層面,我覺得是可以一個一個慢慢來討論跟回應。剛剛老師有提到關於現在任何人都可以拍照,那你怎麼樣去知道你拍的這個照片它最後呈現的結果,它是不是獨特的,我覺得這問題蠻有趣的。我在攝影的過程裡面,不只是攝影這個當下而已,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關聯在一起的,包括最後呈現在現場,包它的括距離,它跟人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高度與大小,它離你近不近,它是不是在一個框內,還是它跳脫一個框,等等,這個觀看的經驗其實是關連到我最初拍攝地當下,並且關連到拍攝完後我跟這個影像的相處過程。其實拍照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跟你拿畫筆,畫出一條線是很簡單的事,可是關鍵在於拍照是一個你去觀看外界的視角,所以對於生活或是周遭你所關注的,會產生你的視角。但在拍完之後,現在的相機已經不是像底片的時代,可能相簿隨時有幾千張照片,那你要選擇哪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是跟拍照當下是一樣重要的。如何整理跟觀看自己的照片,這其實是我從開始拍照好幾年來,一直在摸索的事情,例如我要怎麼樣去把照片歸檔,歸檔方式的定義是什麼,怎麼樣去一步步地去找到你覺得它就是必須要存在在這裡,必須要被張貼在一起,一起說話的那個碎片,我覺得所有過程,它可能會相連。
徐:我覺得剛剛老師提到其實有關於很多不同層面,我覺得是可以一個一個慢慢來討論跟回應。剛剛老師有提到關於現在任何人都可以拍照,那你怎麼樣去知道你拍的這個照片它最後呈現的結果,它是不是獨特的,我覺得這問題蠻有趣的。我在攝影的過程裡面,不只是攝影這個當下而已,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關聯在一起的,包括最後呈現在現場,包它的括距離,它跟人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高度與大小,它離你近不近,它是不是在一個框內,還是它跳脫一個框,等等,這個觀看的經驗其實是關連到我最初拍攝地當下,並且關連到拍攝完後我跟這個影像的相處過程。其實拍照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跟你拿畫筆,畫出一條線是很簡單的事,可是關鍵在於拍照是一個你去觀看外界的視角,所以對於生活或是周遭你所關注的,會產生你的視角。但在拍完之後,現在的相機已經不是像底片的時代,可能相簿隨時有幾千張照片,那你要選擇哪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是跟拍照當下是一樣重要的。如何整理跟觀看自己的照片,這其實是我從開始拍照好幾年來,一直在摸索的事情,例如我要怎麼樣去把照片歸檔,歸檔方式的定義是什麼,怎麼樣去一步步地去找到你覺得它就是必須要存在在這裡,必須要被張貼在一起,一起說話的那個碎片,我覺得所有過程,它可能會相連。
徐:另外一個就是談到攝影這個行為,「影像在我的作品裡面的距離」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跟我運用機械的當下的經驗是有關連的。例如說,我以前一件單張的作品〈From Vauxhall Bridge to Charing Cross〉,是我用三十分鐘攝影曝光,去記錄我在倫敦從一個我家附近的橋走到市中心的一個三十分鐘的路程,它就是記錄了那個當下,我身體移動所顯現的從這地方走到那地方的狀態。在這個作品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距離的層次。在這次的影像我想給大家看到的,它展現的動線的關係,它其實是單向所組成的場景,就是經由這些項展板等等,直立在那邊好像重塑了類似鏡框的舞台讓你可以走進去,這是一個空間上的距離感。另外一個是影像上的距離感,例如說拍攝圓點,看起來像光暈的東西,它所顯示了我在拍攝時候的狀態和距離跟現場的距離是不一樣的,現場它的距離感是比較近的,因為它是我在拍到的時候手在晃動、我當下身體的一個狀態去製造出的東西,那個糊掉的圓點可能就會更具焦在我和對象物之間的距離關係。
黃:所以我們拿起攝影機時到對象物的距離,這就是我們比較傳統的攝影裡面會去思考的問題,隨著我們今天已經到了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所有的影像它可能一方面已經是帶在身上隨著自己的身體的移動在移動,另外一方面,甚至這些影像是在串流裡面的,這些影像其實隨時隨地可以上網然後就在網路上的串流裡面。因為你剛提到,你的這些影像有一些是從你拍下來的影像然後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或者不同的思考,你會去做不同的裁切,然後再去進行要去展出什麼。所以我們會發現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 在我們今天已經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今天跟影像的關係已經密切到了分分秒秒,都在連結,所有人都可以做、所有人都用手機、用機器去拍的時候,其實最後一個攝影展展出的影像是這個人他跟這個影像到底經歷過什麼,它可能是一個行為表演的設計、它也有可能是一個事件的設計,而不是那個決定性的瞬間,那個按下快門的瞬間,這其實還是一個比較古老的美學,可是我會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多關於影像的故事,關於一個影像為什麼會有力量,其實有非常多是透過,剛剛在講的-距離的問題。
以前的攝影跟「重力」很有關係,攝影機就擺在這裡,要不然就是我要有一個很大的機器可以讓我這個拍攝者可以到很奇怪的高度或角度才能拍。可是到了今天在有了數位的能力之後,尤其電腦繪圖整個進入到360度全景空間的捕捉的時候,在理論上他們會說,這叫「無縫」,無縫的一種影像。我們對於影像的擷取應該去想像它是一個全息空間,從哪裡到哪裡它都可以catch到影像的狀態。那要不你就是用一個很高科技的攝影棚來做這件事,可是有另一個我們在感官經驗的思考裡面,它反而會回到一個非常微觀的距離,如果沒有高科技,然後你脫離不了重力的時候,那在這個時代從電動玩具或從很多的介面從VR,其實都知道視角是一個立體球狀的360度空間去捕捉的話,那要怎麼在一個依然活在重力世界的一個沒有太有錢的攝影師,它要如何的呈現這種感受性?在這樣的數位時代,其實就是進入到微觀,因為我們只有進入到微觀的時候才是一個360度的球狀的、到處都可以擷取到的影像。那我會講到那麼抽象,你要能夠去拍出或經營出不同的距離,甚至連結不同的距離,首先你要是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你會有這個時代的感受性,那這也是我會覺得在徐婷的作品裡面,不管是時間或是空間、還有個人的感知都可以,她如何進入到一個重新計算、重新調整、重新去設計,到底最後是什麼樣的影像會出現在展場裡面。也就是從她拍,到進入到展場,都會是有意義的。這件事情我覺得都是整個以藝術發展裡面慢慢累積下來的一種知覺的過程。我覺得每個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給出這張影像或照片的這件事情,變成了今天當代藝術如何去賦予一張照片價值,賦予一張照片它到底可以有多少的感知,是很有關係的。這個部分也是徐婷在她的創作裡面,她用個人實驗的方式在處理這種在當代裡面積累在攝影裡面不同的知覺。
徐:老師剛有提到現代人的包括影像經驗,就是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拍出照片,它甚至也可以是一個全景了,或它是編輯過的,或是電腦截圖等等,老師講的這些,讓我去聯想到我自己在創作的過程其實運用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摸索我的作品,它有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例如說我用很多電腦跳出來的視窗去排列的,或是我直接在資料夾去做一個觀看,或是我也會用3D的軟體去拍現場的各種角度。我覺得經由這些經驗其實都在告訴我們,它已經不是一個可以被拿來當作一個景框內的證據去觀看的攝影狀態,它是更指向當下的,包括影像的創作過程到影像的結果,它都跟你經歷的那個當下有關,這個當下可能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很多當下會形成一個結果一個畫面。關於點線面最一開始我做比較空間式的作品的時候,是在倫敦的一個展覽空間,那空間有一個像是櫥窗的show room,櫥窗型的展場,那時候我拿到這空間後我就覺得這特質很有趣,我就想把我的攝影去拆開來,去一一放置在這空間的不同地方。我那時候就是畫了一個外框的線條,一起形成的另外一個風景,那時候有跟幾個人討論,他們就說其實它裡面有一些線條,有些速度感的事情,還有光點,這種點線面的結構,構成一個畫面的最基本的要素,所以好像這個攝影它可以打破我們紀實之後它最終又變成了另一個畫面,經由這樣子的結構元素去形成。
徐:老師剛有提到現代人的包括影像經驗,就是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拍出照片,它甚至也可以是一個全景了,或它是編輯過的,或是電腦截圖等等,老師講的這些,讓我去聯想到我自己在創作的過程其實運用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摸索我的作品,它有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例如說我用很多電腦跳出來的視窗去排列的,或是我直接在資料夾去做一個觀看,或是我也會用3D的軟體去拍現場的各種角度。我覺得經由這些經驗其實都在告訴我們,它已經不是一個可以被拿來當作一個景框內的證據去觀看的攝影狀態,它是更指向當下的,包括影像的創作過程到影像的結果,它都跟你經歷的那個當下有關,這個當下可能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很多當下會形成一個結果一個畫面。關於點線面最一開始我做比較空間式的作品的時候,是在倫敦的一個展覽空間,那空間有一個像是櫥窗的show room,櫥窗型的展場,那時候我拿到這空間後我就覺得這特質很有趣,我就想把我的攝影去拆開來,去一一放置在這空間的不同地方。我那時候就是畫了一個外框的線條,一起形成的另外一個風景,那時候有跟幾個人討論,他們就說其實它裡面有一些線條,有些速度感的事情,還有光點,這種點線面的結構,構成一個畫面的最基本的要素,所以好像這個攝影它可以打破我們紀實之後它最終又變成了另一個畫面,經由這樣子的結構元素去形成。
徐:我覺得線這件事情,在我創作裡面也是我常運用的一些創作手法。例如說那時候在台南麻豆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作品,因為那個展間是四面環牆的空間,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裝置是在座落在展廳中間,那個裝置經過它的交錯或是它的構成,好像會形成了一種風景。在這個展間裡面我沒有放任和攝影的作品,因為它四面都是窗,就把窗外的影像想像成可以跟這個風景搭配起來的一個影像元素。事實上就是攝影被放在展間裡面的時候,我覺得它很像就是在這個展間開了個窗一樣,可以去遙想那個地方、或是那個畫面,可能發生的事情。在那個裝置上面我畫了細細的線,在大場景裡面它就像是一種軌跡,經由這樣子線條的軌跡,你可以更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在移動。因為你經由某個角度,它可能就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構圖,它是沒有方向性的,包括在《所在》的〈Foggy Mirror〉作品,它可能沒有到這麼全面性,但我覺得它有趣的地方跟這個展覽也有一點相似。它表面上呈現了一個單向的畫面,你可能走到後面發現它其實什麼都不是,它就是一些結構,但是其實你已經在構圖它了,你在走的時候,它已經在不停的成像,不停的不同的樣子出現,這一整個呈現的方式,某方面就是跟我現在生活的狀態是有一點像的,我可能想要經由這個去表達這件事情。
黃:你開始用那些線的問題,我們原本會把這樣一個現代建築的空間當作一個容器,後來在數位化的經驗裡面,大家對於向量、對於繪圖都越來越熟悉的時候,甚至我們在虛擬空間的時間跟在實體空間的時間如果交錯得越來越厲害的時候,只要用線,就可以改變我們對於一個這種剛性空間的感受性。在你的攝影的裝置裡面很直接地用地板上的一條線表達某種感受或某種機會。今天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看攝影影像的狀態或設計都跟數位的經驗很有關係,也就是數位的空間、數位的虛擬介面所給人的一種經驗會有關係。那你剛提到的在倫敦的經驗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你在處理的是一個當下,布列松在處理的也是一個決定性的瞬間,它也是一個當下,可是你們的當下差別很大的地方在於你能夠處理出的當下是它真正出現在一個空間裡面「被固著」的時候,它才會成為當下。所有事情都在流動當中,隨時隨地都可以帶著一個東西走,拍完一個現象就馬上改變了,現在所有東西都變化太快了。對布列松來講,他在拍一個決定性的瞬間的時候,是那個事件最有張力,可以給出讓你以為這個時刻最有張力。比如說有兩個人在打架,有很多人在看,都可以拍出各式各樣有張力的照片,可能只有一張照片可以呈顯這兩個人為什麼打架的那個意義,布列松在追求的就是那個瞬間抓到的張力可以去呈現這個事件背後,某種更為本質事情。如果照我們今天當代的狀態裡面的當下,其實有很多框,今天一個人處理一個影像的時候,是這個世界當下大大小小的框。我們都在經歷不同的框,所以到最後確定下來的是一整個生態系裡面,不管是影像的生態系還是社會的生態系、還是人的生態系,就是在確立一個座標。就很像徐婷的那一張照片它出現在這個時候,它到底是呈現什麼座標?一個攝影師拍出來的一張照片,其實都是存在一個很複雜的生態系裡面才會被看到,這個也是我們今天在看待這樣的攝影、攝影展、影像展的時候,有機會再去發展的部分。
徐:我在想會不會,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型態,讓我們更難意識到「當下」這件事情,上禮拜在進行專訪的時候,就一直問我說,那你覺得儀式感是什麼,那為什麼現代人需要儀式感?我那時候可能也沒有回答得很好,但是我就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就更難去意識到這當下,因為我們隨時都有很多的影像跟資訊一直環繞著我們,所以當一個攝影師要怎麼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去選擇到一個最終它認為是那個當下最好的那個結果?就是我覺得在很多框的世界裡面,會不會最後那個當下它就是在一個模糊的狀態裡面。
黃:每一個人透過它的作品,在某一個地點、空間所能決定出來的那個當下,照理說它的深度決定在於座標上面的關係。這個部分的思考,你就可以走到非常感性,它依然存在著那個座標的系統,即使你表達非常感性非常內在非常隱晦的東西,其實你只要這個座標,只要這個關係可以被呈現的話,它的社會性就會存在。當我在看你在處理這樣的一個空間它其實就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會跟在研究Tillmans的攝影發展會看到的東西,他也很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東西,所以其實到後來,他們現在會很積極的在處理IG的那個狀態。今天我一個影像、我一個筆記本上面的東西,到底我可以產生什麼樣的關係,照理說我們今天在一個數位時代,攝影的影像它會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其實這個是很能夠發展的部分。我覺得台灣在這個部分還思考的非常少,我們應該在台灣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至少還會有五年十年都還在紀實攝影上,這也就會去呈顯台灣本身的一種渴求跟意識形態。台灣的認同問題,這個認同問題如何協商跟折衷,大概紀實的攝影都在處理這些問題。所以,新一代的藝術家或者攝影師,到底要如何去界定他們的影像?當然有一些可以繼續走紀實攝影,當然這是台灣長久以來的焦慮,也是政府最多補助的地方。台灣其實有一直跟國際在走的就是技術,因為不管是跟著代工、技術合作的關係,其實是亦步亦趨的,只是說這部分到底要如何的有機會被呈現出來,技術不是被拿來把那個晚會或慶典弄得更漂亮而已。剛你講到人家在問你的,當下的儀式性,為什麼現代人還需要儀式性?我覺得大部分還會看出儀式性的東西,這大部分都是殘留著過去的印象。現在的當下對我來講,可以從網紅的狀態去理解,你到底要多努力的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去處理訊息,當下是這種感覺,然後他表演得很像一個儀式,但其實早就沒有儀式了,他其實裡面就是一個人在扮演著一個處理器的感覺,在一個當下裡面去處理這個東西,我會是這樣子看。
徐:可能剛提到的某些現況的社會狀態、或是包括網路的這些狀態,它在我的創作裡可能是呈現某種相反的一個方向。很多事情我們可能講求一個功能性,或是大家都很快速地想要知道這些東西好像是什麼,它的意思是什麼,可是在我的作品裡就是什麼都不是,你不知道這個、那個是什麼,我的東西也是「去對象化」。我覺得自己好像一直都在拿著相機,拿著相機是一個比喻,是在創作上我好像一直想要去對焦在一個一個沒有看到的東西上,我一直是一個未對焦的狀態。我剛一開始有想到但沒有講到,就是關於那個「距離」這件事情,我覺得距離它或許在我的創作裡面不只是這個空間或是攝影上面的距離感,我覺得它在時間上也是有距離感的、有座標感的,當然我不確定時間到底是什麼,在這個時代或是宇宙裡面,但是在以我們的生活狀態來講,這個時間還是有些座標存在的。那在看我的作品的時候,如果我們知道它是攝影的話,經由打光線,或是像這次沒有打光,但是它有一個光影的一種狀態存在,那也會去聯想到某個時刻感,或是它是一個凝結住的狀態。
黃:比如在這次的展覽裡面,有兩張就是很像光暈的作品,我們常常會透過光暈跟那種漸層的色系的分布,去判斷這個可能是哪個時代拍的影像。因為每個時代不管是它的輸出或是它的機器的現象,它就會有一個色系的特殊性,甚至不同的地區,它的拍攝因為陽光不一樣。以前底片的時代你就會看到某個地區它拍出來的電影就是比較偏藍,因為陽光跟感光的關係。當我們在拍光暈的時候,當我們直視一個光點的時候,它其實是時間會不見的,因為你如果是拍被光照亮的地方,大家看到那個影像不就會開始去錨定它的時間感:我們看到這個家具是什麼樣的時間、是什麼樣的時代,我們看到這個光是什麼樣的時代、或什麼樣的時間。可是你如果直接就是光點的話,它的時間就不見了,大家就會有太空的想像、宇宙的想像,那裡面就會有一種很不明確的東西開始出現。再加上你後來跟我講說,你其實這個東西是從一張大的照片裡面再裁切下來,所以這裡面就會有一個很複雜的時間的操作。那到底我們從PS(photoshop)裡面的裁切,那個裁切到底在時間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一旦當我們去背的時候到底在時間上發生什麼事情,像這一類的思考就會是我們如何把攝影裡面的那種時間感跟空間感、對於時間空間的思考,把它移轉到電腦的介面上,也就是修圖、然後調色的介面上。因為比如說我接觸到中國的一個錄像的藝術家周滔,那周滔他很有意思,因為他拍的都很像紀錄片的東西,可是他每拍一段東西的時候,他花非常多時間在電腦上修圖,那這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因為通常拍紀錄片其實就是要「記錄」好像當下最真實的那個東西,可是對他來講,我會覺得這就是數位時代不一樣的狀態,數位時代的人已經不像類比時代的人他會以為他拍了一個現場就叫做最真實,我覺得數位時代的人他有一個內在世界的感受,所以他為什麼要去調色,因為他覺得最真實是調色以後的東西,可是他很強調,他不是為了調說他當時看到的顏色是什麼顏色,他要調的是他自己內在當下感受到的顏色。我會覺得這就是一種很不一樣的狀態,那當然其實就會涉及到,你對於你的影像的裁切、調色的過程是不是有可能進一步的這種美學跟技術連結的更進一步的思考。
徐:我覺得老師講的,真的就是我想的。就是我一直以來拍照的時候,我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想法、一樣這樣的疑惑吧,對,在我一開始,其實我小時候就會拿相機來玩了,但我從來都沒有學過把東西拍好或是那種專業技術,就我一直以來都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摸索相機。那我其實就會一直有這個疑惑,就是為什麼攝影書上要教我:你要拍的糊你就得用什麼,你要如何把物件拍好,就是這東西在我心裡一直過不去,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去這幾件,所以我會覺得在這個狀態下,真實是回到那個創作者心中他所認為的真實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