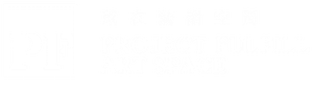The Flare Always Gets Its Way
Yinling Hsu Solo Exhibition
《得逞的火光》許尹齡創作個展
Artist talk record 座談記實
與談人:張晴文(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許尹齡(藝術家)
Artist talk record 座談記實
與談人:張晴文(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許尹齡(藝術家)
張:近期尹齡在就在的個展發表,題目很有意思,叫作「得逞的火光」。這題目可能大家會有點摸不著頭緒,它背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故事?想請妳先談一下這次展覽的題目。
許:這個題目其實陸陸續續想了很久,然後它當然不會是一開始這個系列就有的題目,它是整個系列作完之後累積下來,然後選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名字,因為我這個系列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後來的階段就有跟朋友聊到,一些關於記憶這件事情,我們聊了一個是-基因的記憶,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也很有興趣。那時候我們就聊到用手機,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車上滑手機或是看書的時候,會很想吐這件事情,我朋友說其實這是存在在我們基因記憶裡面的,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類,他們有一個機制,就是當他們不小心誤食一些有毒果實的時候,他們會為了存活直接的吐出來,這是一個演化殘留下來的記憶,就是吃到毒果實的時候吐出來,讓他們得以繼續生存,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看到的那個畫面,就很像以前遠古時代的人類,吃到毒果實之後看到的影像。所以,當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的時候,會誤以為這情況是吃到毒果實了,所以我們下意識會想吐,這就是後來存在在基因裡面的記憶,那時候我朋友說這是天選之人才會有的。後來我就覺得,這個留在基因裡面的記憶很有趣,再加上因為我後來生小孩了,生小孩之後我就很好奇她記得一些什麼事情。我那時候就看了很多關於小孩記憶的書或是一些文章,說小孩他們會記得,能從阿公那代留下來的一些感受,會遺傳到他們的身上,譬如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有一些受虐的記憶,當然長大後會對他的人格有一點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是會持續三代。那時候聽完就覺得很害怕她基因裡面會有這件事情,所以等於小孩只要一哭我就會把她抱起來,然後她就會露出一種得逞的表情,所以那時候「得逞的火光」就是這樣出來的,就是不要在她的基因記憶裡面植入一些什麼不好的東西,這就是當初命名的過程。
張:原來如此。所以這次展覽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從生活經驗來的。我以為坐車一邊滑手機或是一邊看書會覺得想吐,是因為當我們在交通工具上很快速地移動,比如路況顛簸的時候,大腦無法透過視覺很快掌握路況而產生平衡失常的一種生理反應。至於妳說到小孩得逞的笑容,我曾經聽過小孩子有「胎內記憶」,會知道降生在這個地球之前發生的事,尤其當小孩子會說話了但還沒有接收到太多外來知識時,會告訴媽媽她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誕生在這個家庭之類的話。雖然聽起來不太科學,不過根據這種問答的經驗分享,小孩子總是非常篤定地告訴媽媽,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沒在跟你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神奇,但我沒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笑)。
許:還不會亂講話。
張:對對,然後他也還沒有受到那些知識的干擾,如果知識可能會告訴你說,科學來講或是就醫學來講,或者是說理性的分析說,這可能都只是一個胡亂編派的東西,就是還沒有這些東西去刺激或干擾他的時候,很自然他會講出來。我記得我看到的那些分享都是說,小孩子是一副非常篤定的告訴他的,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不是他在跟你開玩笑(許:亂講話)對對對,我就覺得很神奇,但我從來沒有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
許:好,我會抓緊時間點問她。
林:應該可以。
張:問問看她之前有沒有被虐待過(?)
許:對。
(眾人笑)
張:妳在這次個展的創作理念中談到和家人生活、相處的回憶或經驗,包括「得逞的火光」這個展題也是從和小孩的互動而來。家庭似乎是妳從早期至今在創作中一直回應的某個議題,家庭──不管是結婚前或者結婚之後──和妳的創作之間,是否都有一些關聯?
許:從以前的創作,還記得我們十幾年前的一個訪談標題叫作 – 只要對自己誠實(張:對對對),所以如果是我關注的事情一定是從我身邊發生真的讓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的事情、的東西,所以我都會先從最靠近自己的,就是家人、家庭這塊去挖掘,用挖掘自己感受的方式去做。譬如說2009、2010年那時候做過《長壽俱樂部》的創作,其實這個名字是我阿公他經營的一個俱樂部。那一代人,不只是我阿公,像我外公也是,他們那一輩的爸爸會有自己一個樣子,好像他們必須要去符合這個角色,所以他們就會不只做一個事業一個職業,他們會做好多好多事情,光是我兩個阿公他們身上大概就有十幾個不同的角色,所以《長壽俱樂部》時期的作品就會出現不同的角色與空間的組合,每個組合都有點突兀,它代表一種那個時代的氛圍跟社會賦予它們的價值跟角色。後來做了《睡眠博士》系列的創作,那次是關於睡眠的主題是因為我哥哥他在過世之前就有一些睡眠障礙的問題,雖然睡眠障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是很常見的疾病,可是因為睡眠障礙它會影響心理生理很多層面,所以就會延續後面發生了很多關於精神上還有心理上的一些變化跟疾病,所以那時候做了關於《睡眠博士》這個主題就是從睡眠延伸出來的許多故事組成的系列,然後後來一直到那時候在香港Gallery Exit (安全口)做的《標本師》的主題,那是關於情緒,就剛好我哥哥發生意外的那幾年,其實全家人的情緒在一個不可以說的狀態,像是隨時要面對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因為大家都不想要觸碰彼此的痛,所以會連對最親密的家人都需要去扮演成:沒有什麼事情沒有太嚴重的感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哥的房間,我們是一直到去年,我們才敢去開他房間的門去整理,就是我們已經是假裝到這個狀態了,才一直到這兩年才去面對他。所以那時候才做了《標本師》,他是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情緒的人,可能那時候的自己想要扮演成那個角色,所以才設定了那個主題、那個主角,一直到這次關於記憶也是因為我外婆的關係,因為她才會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這個記憶的主題有點抽象,之前還沒有對記憶有興趣的時候,我們可能只會覺得記憶就是我們記得什麼事情、我們不記得什麼事情,可是真的去關注它的時候,會發現其實記憶好像反過來在操作我們,它反而是會變成一個我會讓你有選擇性的記得什麼東西、記得什麼感受、忘記什麼感受的,反客為主的一個角色,這是我做完記憶這個主題自己的感覺,所以一直以來大概創作跟我一開始觸發的感想就是像這個樣子。
許:這個題目其實陸陸續續想了很久,然後它當然不會是一開始這個系列就有的題目,它是整個系列作完之後累積下來,然後選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名字,因為我這個系列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後來的階段就有跟朋友聊到,一些關於記憶這件事情,我們聊了一個是-基因的記憶,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也很有興趣。那時候我們就聊到用手機,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車上滑手機或是看書的時候,會很想吐這件事情,我朋友說其實這是存在在我們基因記憶裡面的,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類,他們有一個機制,就是當他們不小心誤食一些有毒果實的時候,他們會為了存活直接的吐出來,這是一個演化殘留下來的記憶,就是吃到毒果實的時候吐出來,讓他們得以繼續生存,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看到的那個畫面,就很像以前遠古時代的人類,吃到毒果實之後看到的影像。所以,當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的時候,會誤以為這情況是吃到毒果實了,所以我們下意識會想吐,這就是後來存在在基因裡面的記憶,那時候我朋友說這是天選之人才會有的。後來我就覺得,這個留在基因裡面的記憶很有趣,再加上因為我後來生小孩了,生小孩之後我就很好奇她記得一些什麼事情。我那時候就看了很多關於小孩記憶的書或是一些文章,說小孩他們會記得,能從阿公那代留下來的一些感受,會遺傳到他們的身上,譬如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有一些受虐的記憶,當然長大後會對他的人格有一點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是會持續三代。那時候聽完就覺得很害怕她基因裡面會有這件事情,所以等於小孩只要一哭我就會把她抱起來,然後她就會露出一種得逞的表情,所以那時候「得逞的火光」就是這樣出來的,就是不要在她的基因記憶裡面植入一些什麼不好的東西,這就是當初命名的過程。
張:原來如此。所以這次展覽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從生活經驗來的。我以為坐車一邊滑手機或是一邊看書會覺得想吐,是因為當我們在交通工具上很快速地移動,比如路況顛簸的時候,大腦無法透過視覺很快掌握路況而產生平衡失常的一種生理反應。至於妳說到小孩得逞的笑容,我曾經聽過小孩子有「胎內記憶」,會知道降生在這個地球之前發生的事,尤其當小孩子會說話了但還沒有接收到太多外來知識時,會告訴媽媽她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誕生在這個家庭之類的話。雖然聽起來不太科學,不過根據這種問答的經驗分享,小孩子總是非常篤定地告訴媽媽,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沒在跟你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神奇,但我沒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笑)。
許:還不會亂講話。
張:對對,然後他也還沒有受到那些知識的干擾,如果知識可能會告訴你說,科學來講或是就醫學來講,或者是說理性的分析說,這可能都只是一個胡亂編派的東西,就是還沒有這些東西去刺激或干擾他的時候,很自然他會講出來。我記得我看到的那些分享都是說,小孩子是一副非常篤定的告訴他的,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不是他在跟你開玩笑(許:亂講話)對對對,我就覺得很神奇,但我從來沒有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
許:好,我會抓緊時間點問她。
林:應該可以。
張:問問看她之前有沒有被虐待過(?)
許:對。
(眾人笑)
張:妳在這次個展的創作理念中談到和家人生活、相處的回憶或經驗,包括「得逞的火光」這個展題也是從和小孩的互動而來。家庭似乎是妳從早期至今在創作中一直回應的某個議題,家庭──不管是結婚前或者結婚之後──和妳的創作之間,是否都有一些關聯?
許:從以前的創作,還記得我們十幾年前的一個訪談標題叫作 – 只要對自己誠實(張:對對對),所以如果是我關注的事情一定是從我身邊發生真的讓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的事情、的東西,所以我都會先從最靠近自己的,就是家人、家庭這塊去挖掘,用挖掘自己感受的方式去做。譬如說2009、2010年那時候做過《長壽俱樂部》的創作,其實這個名字是我阿公他經營的一個俱樂部。那一代人,不只是我阿公,像我外公也是,他們那一輩的爸爸會有自己一個樣子,好像他們必須要去符合這個角色,所以他們就會不只做一個事業一個職業,他們會做好多好多事情,光是我兩個阿公他們身上大概就有十幾個不同的角色,所以《長壽俱樂部》時期的作品就會出現不同的角色與空間的組合,每個組合都有點突兀,它代表一種那個時代的氛圍跟社會賦予它們的價值跟角色。後來做了《睡眠博士》系列的創作,那次是關於睡眠的主題是因為我哥哥他在過世之前就有一些睡眠障礙的問題,雖然睡眠障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是很常見的疾病,可是因為睡眠障礙它會影響心理生理很多層面,所以就會延續後面發生了很多關於精神上還有心理上的一些變化跟疾病,所以那時候做了關於《睡眠博士》這個主題就是從睡眠延伸出來的許多故事組成的系列,然後後來一直到那時候在香港Gallery Exit (安全口)做的《標本師》的主題,那是關於情緒,就剛好我哥哥發生意外的那幾年,其實全家人的情緒在一個不可以說的狀態,像是隨時要面對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因為大家都不想要觸碰彼此的痛,所以會連對最親密的家人都需要去扮演成:沒有什麼事情沒有太嚴重的感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哥的房間,我們是一直到去年,我們才敢去開他房間的門去整理,就是我們已經是假裝到這個狀態了,才一直到這兩年才去面對他。所以那時候才做了《標本師》,他是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情緒的人,可能那時候的自己想要扮演成那個角色,所以才設定了那個主題、那個主角,一直到這次關於記憶也是因為我外婆的關係,因為她才會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這個記憶的主題有點抽象,之前還沒有對記憶有興趣的時候,我們可能只會覺得記憶就是我們記得什麼事情、我們不記得什麼事情,可是真的去關注它的時候,會發現其實記憶好像反過來在操作我們,它反而是會變成一個我會讓你有選擇性的記得什麼東西、記得什麼感受、忘記什麼感受的,反客為主的一個角色,這是我做完記憶這個主題自己的感覺,所以一直以來大概創作跟我一開始觸發的感想就是像這個樣子。
張:近期尹齡在就在的個展發表,題目很有意思,叫作「得逞的火光」。這題目可能大家會有點摸不著頭緒,它背後是否有什麼樣的故事?想請妳先談一下這次展覽的題目。
許:這個題目其實陸陸續續想了很久,然後它當然不會是一開始這個系列就有的題目,它是整個系列作完之後累積下來,然後選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名字,因為我這個系列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後來的階段就有跟朋友聊到,一些關於記憶這件事情,我們聊了一個是-基因的記憶,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也很有興趣。那時候我們就聊到用手機,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車上滑手機或是看書的時候,會很想吐這件事情,我朋友說其實這是存在在我們基因記憶裡面的,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類,他們有一個機制,就是當他們不小心誤食一些有毒果實的時候,他們會為了存活直接的吐出來,這是一個演化殘留下來的記憶,就是吃到毒果實的時候吐出來,讓他們得以繼續生存,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看到的那個畫面,就很像以前遠古時代的人類,吃到毒果實之後看到的影像。所以,當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的時候,會誤以為這情況是吃到毒果實了,所以我們下意識會想吐,這就是後來存在在基因裡面的記憶,那時候我朋友說這是天選之人才會有的。後來我就覺得,這個留在基因裡面的記憶很有趣,再加上因為我後來生小孩了,生小孩之後我就很好奇她記得一些什麼事情。我那時候就看了很多關於小孩記憶的書或是一些文章,說小孩他們會記得,能從阿公那代留下來的一些感受,會遺傳到他們的身上,譬如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有一些受虐的記憶,當然長大後會對他的人格有一點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是會持續三代。那時候聽完就覺得很害怕她基因裡面會有這件事情,所以等於小孩只要一哭我就會把她抱起來,然後她就會露出一種得逞的表情,所以那時候「得逞的火光」就是這樣出來的,就是不要在她的基因記憶裡面植入一些什麼不好的東西,這就是當初命名的過程。
張:原來如此。所以這次展覽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從生活經驗來的。我以為坐車一邊滑手機或是一邊看書會覺得想吐,是因為當我們在交通工具上很快速地移動,比如路況顛簸的時候,大腦無法透過視覺很快掌握路況而產生平衡失常的一種生理反應。至於妳說到小孩得逞的笑容,我曾經聽過小孩子有「胎內記憶」,會知道降生在這個地球之前發生的事,尤其當小孩子會說話了但還沒有接收到太多外來知識時,會告訴媽媽她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誕生在這個家庭之類的話。雖然聽起來不太科學,不過根據這種問答的經驗分享,小孩子總是非常篤定地告訴媽媽,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沒在跟你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神奇,但我沒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笑)。
許:還不會亂講話。
張:對對,然後他也還沒有受到那些知識的干擾,如果知識可能會告訴你說,科學來講或是就醫學來講,或者是說理性的分析說,這可能都只是一個胡亂編派的東西,就是還沒有這些東西去刺激或干擾他的時候,很自然他會講出來。我記得我看到的那些分享都是說,小孩子是一副非常篤定的告訴他的,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不是他在跟你開玩笑(許:亂講話)對對對,我就覺得很神奇,但我從來沒有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
許:好,我會抓緊時間點問她。
林:應該可以。
張:問問看她之前有沒有被虐待過(?)
許:對。
(眾人笑)
張:妳在這次個展的創作理念中談到和家人生活、相處的回憶或經驗,包括「得逞的火光」這個展題也是從和小孩的互動而來。家庭似乎是妳從早期至今在創作中一直回應的某個議題,家庭──不管是結婚前或者結婚之後──和妳的創作之間,是否都有一些關聯?
許:從以前的創作,還記得我們十幾年前的一個訪談標題叫作 – 只要對自己誠實(張:對對對),所以如果是我關注的事情一定是從我身邊發生真的讓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的事情、的東西,所以我都會先從最靠近自己的,就是家人、家庭這塊去挖掘,用挖掘自己感受的方式去做。譬如說2009、2010年那時候做過《長壽俱樂部》的創作,其實這個名字是我阿公他經營的一個俱樂部。那一代人,不只是我阿公,像我外公也是,他們那一輩的爸爸會有自己一個樣子,好像他們必須要去符合這個角色,所以他們就會不只做一個事業一個職業,他們會做好多好多事情,光是我兩個阿公他們身上大概就有十幾個不同的角色,所以《長壽俱樂部》時期的作品就會出現不同的角色與空間的組合,每個組合都有點突兀,它代表一種那個時代的氛圍跟社會賦予它們的價值跟角色。後來做了《睡眠博士》系列的創作,那次是關於睡眠的主題是因為我哥哥他在過世之前就有一些睡眠障礙的問題,雖然睡眠障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是很常見的疾病,可是因為睡眠障礙它會影響心理生理很多層面,所以就會延續後面發生了很多關於精神上還有心理上的一些變化跟疾病,所以那時候做了關於《睡眠博士》這個主題就是從睡眠延伸出來的許多故事組成的系列,然後後來一直到那時候在香港Gallery Exit (安全口)做的《標本師》的主題,那是關於情緒,就剛好我哥哥發生意外的那幾年,其實全家人的情緒在一個不可以說的狀態,像是隨時要面對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因為大家都不想要觸碰彼此的痛,所以會連對最親密的家人都需要去扮演成:沒有什麼事情沒有太嚴重的感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哥的房間,我們是一直到去年,我們才敢去開他房間的門去整理,就是我們已經是假裝到這個狀態了,才一直到這兩年才去面對他。所以那時候才做了《標本師》,他是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情緒的人,可能那時候的自己想要扮演成那個角色,所以才設定了那個主題、那個主角,一直到這次關於記憶也是因為我外婆的關係,因為她才會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這個記憶的主題有點抽象,之前還沒有對記憶有興趣的時候,我們可能只會覺得記憶就是我們記得什麼事情、我們不記得什麼事情,可是真的去關注它的時候,會發現其實記憶好像反過來在操作我們,它反而是會變成一個我會讓你有選擇性的記得什麼東西、記得什麼感受、忘記什麼感受的,反客為主的一個角色,這是我做完記憶這個主題自己的感覺,所以一直以來大概創作跟我一開始觸發的感想就是像這個樣子。
許:這個題目其實陸陸續續想了很久,然後它當然不會是一開始這個系列就有的題目,它是整個系列作完之後累積下來,然後選一個最適合它們的名字,因為我這個系列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後來的階段就有跟朋友聊到,一些關於記憶這件事情,我們聊了一個是-基因的記憶,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也很有興趣。那時候我們就聊到用手機,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車上滑手機或是看書的時候,會很想吐這件事情,我朋友說其實這是存在在我們基因記憶裡面的,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類,他們有一個機制,就是當他們不小心誤食一些有毒果實的時候,他們會為了存活直接的吐出來,這是一個演化殘留下來的記憶,就是吃到毒果實的時候吐出來,讓他們得以繼續生存,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看到的那個畫面,就很像以前遠古時代的人類,吃到毒果實之後看到的影像。所以,當我們在車上滑手機的時候,會誤以為這情況是吃到毒果實了,所以我們下意識會想吐,這就是後來存在在基因裡面的記憶,那時候我朋友說這是天選之人才會有的。後來我就覺得,這個留在基因裡面的記憶很有趣,再加上因為我後來生小孩了,生小孩之後我就很好奇她記得一些什麼事情。我那時候就看了很多關於小孩記憶的書或是一些文章,說小孩他們會記得,能從阿公那代留下來的一些感受,會遺傳到他們的身上,譬如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有一些受虐的記憶,當然長大後會對他的人格有一點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是會持續三代。那時候聽完就覺得很害怕她基因裡面會有這件事情,所以等於小孩只要一哭我就會把她抱起來,然後她就會露出一種得逞的表情,所以那時候「得逞的火光」就是這樣出來的,就是不要在她的基因記憶裡面植入一些什麼不好的東西,這就是當初命名的過程。
張:原來如此。所以這次展覽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從生活經驗來的。我以為坐車一邊滑手機或是一邊看書會覺得想吐,是因為當我們在交通工具上很快速地移動,比如路況顛簸的時候,大腦無法透過視覺很快掌握路況而產生平衡失常的一種生理反應。至於妳說到小孩得逞的笑容,我曾經聽過小孩子有「胎內記憶」,會知道降生在這個地球之前發生的事,尤其當小孩子會說話了但還沒有接收到太多外來知識時,會告訴媽媽她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誕生在這個家庭之類的話。雖然聽起來不太科學,不過根據這種問答的經驗分享,小孩子總是非常篤定地告訴媽媽,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沒在跟你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神奇,但我沒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笑)。
許:還不會亂講話。
張:對對,然後他也還沒有受到那些知識的干擾,如果知識可能會告訴你說,科學來講或是就醫學來講,或者是說理性的分析說,這可能都只是一個胡亂編派的東西,就是還沒有這些東西去刺激或干擾他的時候,很自然他會講出來。我記得我看到的那些分享都是說,小孩子是一副非常篤定的告訴他的,就是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喔,不是他在跟你開玩笑(許:亂講話)對對對,我就覺得很神奇,但我從來沒有問過我小孩這個問題。
許:好,我會抓緊時間點問她。
林:應該可以。
張:問問看她之前有沒有被虐待過(?)
許:對。
(眾人笑)
張:妳在這次個展的創作理念中談到和家人生活、相處的回憶或經驗,包括「得逞的火光」這個展題也是從和小孩的互動而來。家庭似乎是妳從早期至今在創作中一直回應的某個議題,家庭──不管是結婚前或者結婚之後──和妳的創作之間,是否都有一些關聯?
許:從以前的創作,還記得我們十幾年前的一個訪談標題叫作 – 只要對自己誠實(張:對對對),所以如果是我關注的事情一定是從我身邊發生真的讓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的事情、的東西,所以我都會先從最靠近自己的,就是家人、家庭這塊去挖掘,用挖掘自己感受的方式去做。譬如說2009、2010年那時候做過《長壽俱樂部》的創作,其實這個名字是我阿公他經營的一個俱樂部。那一代人,不只是我阿公,像我外公也是,他們那一輩的爸爸會有自己一個樣子,好像他們必須要去符合這個角色,所以他們就會不只做一個事業一個職業,他們會做好多好多事情,光是我兩個阿公他們身上大概就有十幾個不同的角色,所以《長壽俱樂部》時期的作品就會出現不同的角色與空間的組合,每個組合都有點突兀,它代表一種那個時代的氛圍跟社會賦予它們的價值跟角色。後來做了《睡眠博士》系列的創作,那次是關於睡眠的主題是因為我哥哥他在過世之前就有一些睡眠障礙的問題,雖然睡眠障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是很常見的疾病,可是因為睡眠障礙它會影響心理生理很多層面,所以就會延續後面發生了很多關於精神上還有心理上的一些變化跟疾病,所以那時候做了關於《睡眠博士》這個主題就是從睡眠延伸出來的許多故事組成的系列,然後後來一直到那時候在香港Gallery Exit (安全口)做的《標本師》的主題,那是關於情緒,就剛好我哥哥發生意外的那幾年,其實全家人的情緒在一個不可以說的狀態,像是隨時要面對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因為大家都不想要觸碰彼此的痛,所以會連對最親密的家人都需要去扮演成:沒有什麼事情沒有太嚴重的感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哥的房間,我們是一直到去年,我們才敢去開他房間的門去整理,就是我們已經是假裝到這個狀態了,才一直到這兩年才去面對他。所以那時候才做了《標本師》,他是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情緒的人,可能那時候的自己想要扮演成那個角色,所以才設定了那個主題、那個主角,一直到這次關於記憶也是因為我外婆的關係,因為她才會想要做關於記憶的主題。這個記憶的主題有點抽象,之前還沒有對記憶有興趣的時候,我們可能只會覺得記憶就是我們記得什麼事情、我們不記得什麼事情,可是真的去關注它的時候,會發現其實記憶好像反過來在操作我們,它反而是會變成一個我會讓你有選擇性的記得什麼東西、記得什麼感受、忘記什麼感受的,反客為主的一個角色,這是我做完記憶這個主題自己的感覺,所以一直以來大概創作跟我一開始觸發的感想就是像這個樣子。
張:去年妳生了小孩,從懷孕到生小孩這過程時間其實也很長(許:真的)。變成媽媽這個身分,我自己覺得一時之間很難說清楚,一切都是新的經驗,手忙腳亂之中不停接下新的挑戰、新的任務,時間就這樣過去了(許:對),根本沒那個時間意識到自己身分不同了、有什麼想法不一樣(許:不會)。對一個育兒的媽媽來說,時間是最寶貴的,除了工作時間不容易之外,在妳的創作上,是不是有些明顯的改變?包括材料、繪畫語言的差異等?
許:就是媒材上是一定都會改變,改變最大的是媒介的油,因為從懷孕之後到現在,小孩有時候會去工作室,所以我就都沒有再使用那種有揮發性的溶劑、調和劑,單純用油的結果,它就變成了把整個創作節奏慢下來的一個媒介,我覺得也不是我有意要慢下來,但它會讓創作的節奏慢下來,因為它不能很滑順的推過去,它就是必須慢慢的、慢慢的去累積它,但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過程,因為我才真的去回憶起,就像晴文剛剛說的,生了小孩之後真的是每天都在打仗,我才開始回憶懷孕的過程,我覺得真的很感謝我的小孩讓我整個人都慢下來,因為我以前就連去坐捷運,捷運明明三五分鐘一班,我都還是會從手扶梯左邊走過去,然後紅綠燈也是,只要快到紅燈我還是會跑過去,可是懷孕之後就真的都改掉這個習慣。就連現在,你的生活一直在很快速的前進可是你整個人的感受是慢下來的,我覺得它好像也有一點體現在這次的創作裡面,它們是比較平穩的,感覺好像比較溫柔一點。有一些色調,有時候我自己畫完會一直回頭看,因為在一直回頭看那種感受就真的好溫柔這是誰,然後有時候翻到以前的作品跟現在的色調就覺得怎麼會調出這個顏色,不可思議,因為懷孕之後的改變,我有點懷疑自己,所以我會一直把它再拿出來看,去確認了我現在是喜歡這個樣子的,我覺得這是蠻妙的事情。我以前很喜歡組織自己,就是連創作都是,我會想要把每一個東西都先規劃好然後去做,它應該是什麼樣子我會想要真的最後呈現出來的樣子,對,我以前都會畫一個小小的東西然後再把它畫到畫布上,可是現在也沒辦法做這種事情了,就是連畫那個小小的東西最後也都不是長那個樣子了,它是一個改變。
張:從新作看來,黏著性確實比較高,之前會覺得妳作品整體的流動性會高一點。這次看起來是很沉穩的,但不是沉重,仍有妳向來一派輕鬆的樣子,是被掌控得很好的,不是浮動感。這可能跟材料有關,或者是心境的變化吧。
許:就是一個人的節奏,就這樣被改變了,覺得很奇妙呵呵
張:被迫改變!我記得妳在幾年前的一次個展裡,所有作品都是很有劇場感的畫面,像是被安排好的一場表演。最近這幾年,手機拍照非常方便,大家一天到晚都在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生活,或者說回應世界。當人們很習慣用影像去處理經驗,也創造了一個影像爆量的環境,我很好奇妳對這樣的狀態有何看法?因為我總覺得妳的作品相對於快速的、大量的、瑣碎的視覺感,會給人較為安靜的、沉穩的氛圍。這和妳接觸視覺文化或影像生活的經驗是不是有些關係?特別是你先生是攝影工作者,對嗎?
許:對
張:他從事攝影創作,或者商業攝影?
許:都有
張:妳對於現在這種影像每分每秒都佔據著生活的狀態,有特別的感受嗎?就妳這樣長期投入繪畫的人而言,會對此特別排斥嗎?
許:不會排斥,可是就會知道自己跟不上這個節奏。我覺得它是需要你這個人的特質裡面,有這種基因的人才辦得到的,就是像那些很可以在網路上分享自己事情的人,他可以立刻處理好所有的影像,然後立刻發出了內容。如果說我今天拍了一個影像,我會想要修它,會去假想我現在看到這個影像跟我分享出去大家看到它的感受,大家看到這個感受會聯想到我是什麼樣的人,或者是他們可以接收到我想要傳達、對這個影像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嗎?我會想這麼多,從此以後這些東西就不會PO了,呵呵呵,它就會胎死在我的手機裡面。像我記錄我的小孩很多事情,我幾乎是每天都在記錄她,然後就想,好我要來PO了,可是就是想說那這樣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是曬嬰魔人?我不想讓大家知道藝術家許尹齡是曬嬰魔人,這跟我自己想像給自己的人格設定不太一樣,然後它就會這樣死在我的手機裡面。(張:我也不喜歡PO小孩)對,而且最恐怖的是,有一次我就跟我真的很 要好的朋友討論到這件事情,我就說那你們看到小孩的時候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然後他就說,我其實一點都不覺得很可愛,不懂爸媽為什麼會覺得可愛,然後聽完就覺得天哪好恐怖喔,如果別人這樣想我的小孩,我可能會承受不住,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跟大家想像想像出來的網路世界,跟那些可以跟上網路節奏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樣的,大家都在自己的平行世界裡面,我覺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張:真的。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妳比較擅長、也習慣慢速的影像表現。
許:對。就如果真的有一天把它分享出去那也真的是,方方面面自己都準備好了的樣子,它有一點像是個人網站的那種處理方式。
許:就是媒材上是一定都會改變,改變最大的是媒介的油,因為從懷孕之後到現在,小孩有時候會去工作室,所以我就都沒有再使用那種有揮發性的溶劑、調和劑,單純用油的結果,它就變成了把整個創作節奏慢下來的一個媒介,我覺得也不是我有意要慢下來,但它會讓創作的節奏慢下來,因為它不能很滑順的推過去,它就是必須慢慢的、慢慢的去累積它,但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過程,因為我才真的去回憶起,就像晴文剛剛說的,生了小孩之後真的是每天都在打仗,我才開始回憶懷孕的過程,我覺得真的很感謝我的小孩讓我整個人都慢下來,因為我以前就連去坐捷運,捷運明明三五分鐘一班,我都還是會從手扶梯左邊走過去,然後紅綠燈也是,只要快到紅燈我還是會跑過去,可是懷孕之後就真的都改掉這個習慣。就連現在,你的生活一直在很快速的前進可是你整個人的感受是慢下來的,我覺得它好像也有一點體現在這次的創作裡面,它們是比較平穩的,感覺好像比較溫柔一點。有一些色調,有時候我自己畫完會一直回頭看,因為在一直回頭看那種感受就真的好溫柔這是誰,然後有時候翻到以前的作品跟現在的色調就覺得怎麼會調出這個顏色,不可思議,因為懷孕之後的改變,我有點懷疑自己,所以我會一直把它再拿出來看,去確認了我現在是喜歡這個樣子的,我覺得這是蠻妙的事情。我以前很喜歡組織自己,就是連創作都是,我會想要把每一個東西都先規劃好然後去做,它應該是什麼樣子我會想要真的最後呈現出來的樣子,對,我以前都會畫一個小小的東西然後再把它畫到畫布上,可是現在也沒辦法做這種事情了,就是連畫那個小小的東西最後也都不是長那個樣子了,它是一個改變。
張:從新作看來,黏著性確實比較高,之前會覺得妳作品整體的流動性會高一點。這次看起來是很沉穩的,但不是沉重,仍有妳向來一派輕鬆的樣子,是被掌控得很好的,不是浮動感。這可能跟材料有關,或者是心境的變化吧。
許:就是一個人的節奏,就這樣被改變了,覺得很奇妙呵呵
張:被迫改變!我記得妳在幾年前的一次個展裡,所有作品都是很有劇場感的畫面,像是被安排好的一場表演。最近這幾年,手機拍照非常方便,大家一天到晚都在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生活,或者說回應世界。當人們很習慣用影像去處理經驗,也創造了一個影像爆量的環境,我很好奇妳對這樣的狀態有何看法?因為我總覺得妳的作品相對於快速的、大量的、瑣碎的視覺感,會給人較為安靜的、沉穩的氛圍。這和妳接觸視覺文化或影像生活的經驗是不是有些關係?特別是你先生是攝影工作者,對嗎?
許:對
張:他從事攝影創作,或者商業攝影?
許:都有
張:妳對於現在這種影像每分每秒都佔據著生活的狀態,有特別的感受嗎?就妳這樣長期投入繪畫的人而言,會對此特別排斥嗎?
許:不會排斥,可是就會知道自己跟不上這個節奏。我覺得它是需要你這個人的特質裡面,有這種基因的人才辦得到的,就是像那些很可以在網路上分享自己事情的人,他可以立刻處理好所有的影像,然後立刻發出了內容。如果說我今天拍了一個影像,我會想要修它,會去假想我現在看到這個影像跟我分享出去大家看到它的感受,大家看到這個感受會聯想到我是什麼樣的人,或者是他們可以接收到我想要傳達、對這個影像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嗎?我會想這麼多,從此以後這些東西就不會PO了,呵呵呵,它就會胎死在我的手機裡面。像我記錄我的小孩很多事情,我幾乎是每天都在記錄她,然後就想,好我要來PO了,可是就是想說那這樣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是曬嬰魔人?我不想讓大家知道藝術家許尹齡是曬嬰魔人,這跟我自己想像給自己的人格設定不太一樣,然後它就會這樣死在我的手機裡面。(張:我也不喜歡PO小孩)對,而且最恐怖的是,有一次我就跟我真的很 要好的朋友討論到這件事情,我就說那你們看到小孩的時候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然後他就說,我其實一點都不覺得很可愛,不懂爸媽為什麼會覺得可愛,然後聽完就覺得天哪好恐怖喔,如果別人這樣想我的小孩,我可能會承受不住,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跟大家想像想像出來的網路世界,跟那些可以跟上網路節奏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樣的,大家都在自己的平行世界裡面,我覺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張:真的。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妳比較擅長、也習慣慢速的影像表現。
許:對。就如果真的有一天把它分享出去那也真的是,方方面面自己都準備好了的樣子,它有一點像是個人網站的那種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