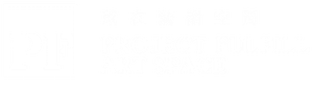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
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 個展
2023.02.04 - 2023.03.04 |
座談會 Artist Talk: 2023.02.11 (六) Sat. 3pm
與談人 Panelists: 顧世勇 Ku Shih-Yung 沈裕昌 Shen Yu-Chang 蔡芝其 Tsai Chih-Chi |
顧世勇,沈裕昌,蔡芝其
蔡芝其:
謝謝大家來座談,剛剛我有介紹過顧世勇老師、 跟沈裕昌老師,我是芝其。我先前情提要一下,我的作品主要的媒材是繪畫,然後繪畫可能是相對其他當代媒材更直觀一點的。因為它跟身體、或是跟創作者本身的連結可能更直接一點,有“手部”這種不可抗力的部分。我覺得「直觀」這個部分對我來說也是重要的,就是它對我來說是有用的。因為它是我在選擇的傾向上,用繪畫的語言去表現或是去轉譯的一部分。然後第二個提要就是,因為是繪畫,所以直接地就是關於“作品描繪的對象”跟“素材”。雖然我的繪畫在我這邊還是有一些演進或是變化,但我一直以來的繪畫素材就是就是屏幕上的那些數位影像,就是我們可以用手機或是在網路上瀏覽的那些大量的“他人的生活影像”,或是我們會隨處擷取然後分享的那些日常影像。
那就會面臨到“如何篩選”。為了不去篩選它,還是有一個“不選擇的必要選擇”。就是我會選的是比較普遍性一點的構圖,可能是比較能夠有既定的、照片中的影像,譬如說「人」、「人景」、「合照」或是,人可能站在海景中間。但我不會特別去強化說我就是要呈現這些影像,因為我其實沒有要批判或是表達景觀社會之類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我是作為沈浸在瀏覽裡面的一份子,也就是我的感知是這樣,所以在我的選擇裡面是這樣的傾向。我的前情提要可能先到這裡,等一下如果有問到我我再回答,還可以分享一些感性的想法。
沈裕昌:
我想我們輕鬆一點,大家有什麼想法就聊一聊。芝其這次展覽的作品對我來說,討論起來特別的地方,剛剛芝其提到「繪畫」,然後她也認為她的作品是繪畫。我先不要做一個全面的、普遍性的論斷,不要說「所有繪畫」,我就先說「芝其的繪畫」。
以她的繪畫來說,我從她剛剛的這個討論裡面,有聽出一個我覺得重要的地方,傳統上我們在討論一個「對象」的時候,所謂「對象」,就是‘object’,那個‘ject’有投射出去的意思、丟到前面的意思。所以我們在討論一個對象的時候,我們要站在它的對面、或是站在它的外面,我們不跟這個東西站在一起。可是一站在它的外面去看它,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如果我跟那個東西明明是在同一個地方的,比如說我們都是“存在者”,然後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是可視的對象,如果我們都是一樣的東西,但你在討論它的時候就把你自己放到外面,這時候就會有一個悖論就是:「你如何假裝跟它在一起?或假裝不跟它在一起?」。
那芝其剛剛的討論,她強調她在這個圖像經驗“裡面”。我這樣說的這個「圖像經驗」就是大家經常做的這一個手指運動,就是拿著手機然後滑這些圖像。這個圖像,第一個就是它量非常大,她沒有特別去限定這個圖像的類型,但是她用了一個難以限定的、難以說明的類型。就是說一般的這種社群的、網站上的這些圖像,然後它被我們大量瀏覽,然後在瀏覽它的時候,其實所有人都會有這個經驗,可是當我們要把這個經驗對象化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去做篩選,我要什麼圖像或不要什麼圖像。
可是芝其她的姿態是特別的—她不採取選擇,也就是說她不站在這個圖像的對面或外面,她站在圖像的裡面,因此我們如何能夠去想像 「我們不把一個東西對象化,而是跟那個東西站在一起去想它」,這時候就會遇到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了,就是說我不能採取任何特定的方法,因為我一採取特定的方法,那個方法就會把我跟對象拉開來—即便它是一個繪畫方法,或者說是一個藝術創作的方法。它會把我跟對象拉開一個距離,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我們剛說的—所謂形上學的這種悖謬會出現。那我要跟它站在一起,我該採取的如果不是一個方法會是什麼?所以她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在很多討論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語言的限度,因此只要把東西放到對面,中間置入方法,就能讓它像自動化一樣—這是一種思想的自動化,反而可以讓它很快的按照一種邏輯進行。
可是她今天做的是一種對於自動化的破壞,那你說破壞自動化的思想,反而才是真正的想東西的方式。意思是說我阻斷它,我不讓它照著程序跑。然後她的方式是說:我選擇跟那個圖像經驗站在一起,而且我不試著用一種方法論的方式去處理這些作品,我不是設計一個函數讓圖像跑了之後自動出來。所以有關於她到底採取了什麼樣的圖像方式,就是使用語言、否棄語言的,慢慢接近這樣子,然後這個其實也表現在她處理畫面的、或者說處理顏料的方式。我覺得我們待會可以一邊在語言和概念上,一邊在她作品的這些圖像也好,或者說她處理顏料的方式也好,我們可以不斷地在這兩端往返,然後去貼近她想要講的東西。那是不是請顧老師?
謝謝大家來座談,剛剛我有介紹過顧世勇老師、 跟沈裕昌老師,我是芝其。我先前情提要一下,我的作品主要的媒材是繪畫,然後繪畫可能是相對其他當代媒材更直觀一點的。因為它跟身體、或是跟創作者本身的連結可能更直接一點,有“手部”這種不可抗力的部分。我覺得「直觀」這個部分對我來說也是重要的,就是它對我來說是有用的。因為它是我在選擇的傾向上,用繪畫的語言去表現或是去轉譯的一部分。然後第二個提要就是,因為是繪畫,所以直接地就是關於“作品描繪的對象”跟“素材”。雖然我的繪畫在我這邊還是有一些演進或是變化,但我一直以來的繪畫素材就是就是屏幕上的那些數位影像,就是我們可以用手機或是在網路上瀏覽的那些大量的“他人的生活影像”,或是我們會隨處擷取然後分享的那些日常影像。
那就會面臨到“如何篩選”。為了不去篩選它,還是有一個“不選擇的必要選擇”。就是我會選的是比較普遍性一點的構圖,可能是比較能夠有既定的、照片中的影像,譬如說「人」、「人景」、「合照」或是,人可能站在海景中間。但我不會特別去強化說我就是要呈現這些影像,因為我其實沒有要批判或是表達景觀社會之類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我是作為沈浸在瀏覽裡面的一份子,也就是我的感知是這樣,所以在我的選擇裡面是這樣的傾向。我的前情提要可能先到這裡,等一下如果有問到我我再回答,還可以分享一些感性的想法。
沈裕昌:
我想我們輕鬆一點,大家有什麼想法就聊一聊。芝其這次展覽的作品對我來說,討論起來特別的地方,剛剛芝其提到「繪畫」,然後她也認為她的作品是繪畫。我先不要做一個全面的、普遍性的論斷,不要說「所有繪畫」,我就先說「芝其的繪畫」。
以她的繪畫來說,我從她剛剛的這個討論裡面,有聽出一個我覺得重要的地方,傳統上我們在討論一個「對象」的時候,所謂「對象」,就是‘object’,那個‘ject’有投射出去的意思、丟到前面的意思。所以我們在討論一個對象的時候,我們要站在它的對面、或是站在它的外面,我們不跟這個東西站在一起。可是一站在它的外面去看它,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如果我跟那個東西明明是在同一個地方的,比如說我們都是“存在者”,然後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是可視的對象,如果我們都是一樣的東西,但你在討論它的時候就把你自己放到外面,這時候就會有一個悖論就是:「你如何假裝跟它在一起?或假裝不跟它在一起?」。
那芝其剛剛的討論,她強調她在這個圖像經驗“裡面”。我這樣說的這個「圖像經驗」就是大家經常做的這一個手指運動,就是拿著手機然後滑這些圖像。這個圖像,第一個就是它量非常大,她沒有特別去限定這個圖像的類型,但是她用了一個難以限定的、難以說明的類型。就是說一般的這種社群的、網站上的這些圖像,然後它被我們大量瀏覽,然後在瀏覽它的時候,其實所有人都會有這個經驗,可是當我們要把這個經驗對象化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去做篩選,我要什麼圖像或不要什麼圖像。
可是芝其她的姿態是特別的—她不採取選擇,也就是說她不站在這個圖像的對面或外面,她站在圖像的裡面,因此我們如何能夠去想像 「我們不把一個東西對象化,而是跟那個東西站在一起去想它」,這時候就會遇到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了,就是說我不能採取任何特定的方法,因為我一採取特定的方法,那個方法就會把我跟對象拉開來—即便它是一個繪畫方法,或者說是一個藝術創作的方法。它會把我跟對象拉開一個距離,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我們剛說的—所謂形上學的這種悖謬會出現。那我要跟它站在一起,我該採取的如果不是一個方法會是什麼?所以她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在很多討論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語言的限度,因此只要把東西放到對面,中間置入方法,就能讓它像自動化一樣—這是一種思想的自動化,反而可以讓它很快的按照一種邏輯進行。
可是她今天做的是一種對於自動化的破壞,那你說破壞自動化的思想,反而才是真正的想東西的方式。意思是說我阻斷它,我不讓它照著程序跑。然後她的方式是說:我選擇跟那個圖像經驗站在一起,而且我不試著用一種方法論的方式去處理這些作品,我不是設計一個函數讓圖像跑了之後自動出來。所以有關於她到底採取了什麼樣的圖像方式,就是使用語言、否棄語言的,慢慢接近這樣子,然後這個其實也表現在她處理畫面的、或者說處理顏料的方式。我覺得我們待會可以一邊在語言和概念上,一邊在她作品的這些圖像也好,或者說她處理顏料的方式也好,我們可以不斷地在這兩端往返,然後去貼近她想要講的東西。那是不是請顧老師?
顧世勇:
大家好,我因為從花蓮過來,萬一狀況不太好的話,可以念那一篇文章(fb發文)。一開始的時候我是說「看就好了。」,事實上繪畫本來就看就好了,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在這邊,還是要說一點東西,所以還是用語言去詮釋。
那因為繪畫本身它的語言,跟我們學的語言當然不一樣,繪畫它本身就是一種語言,不是還要透過語言去詮釋它。我覺得看她的作品其實很直接,就誠如她自己說的「繪畫是一個事實」。從她有一些故意在畫旁邊,做了一個很短的檯座,就是她已經不太區分所謂平面跟立體,她一直告訴我們「繪畫作為一個事實」在那個地方,就跟這些檯座啊,可以看得出來。她的畫雖然有一些掛在牆壁上,但有一些是擺在這些像台座。她一直暗示我們,其實這個空間裡面的這些東西是事實,不是像以前,繪畫住在一個幻覺中、裱框,製造一個幻覺。她作品裡面完全沒有幻覺,就是你在這個地方,你看到的東西,這些材質、物質,還有這些平面給你直接的感受。我想這個就是她作品裡面,我們直接面對的。我們不必要在畫面看到她要說什麼故事,或是她要再現什麼我們曾經看過的東西,她只是全部都給它事實,這一部分,就是她很清楚她在表達這一部分。
因為她作品基本上,我認為是這樣,雖然是2D的,但是它擺在一個空間裡面,事實上所有東西都動員起來了,它就變成不再孤立了。也就是說它不再是內在平面的問題,它變成是整個框,就是它整個環境的「這個」。事實上我當然知道她之前作畫的時候,是擺平了畫,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說她的「視域」很重要,她畫畫不是像以前立起來的,立起來基本上就是製造幻覺,因為立起來就表示,你跟繪畫的關係有一定的距離。然後你會透過視覺去製造一個類似三維的空間,不管那邊是抽象或是空間暗示的,但它就意味著你跟它的關係,就是製造一個「這裡」跟「那裡」的關係。可是她在作畫上面有一點意思的是她「擺平了它」,她在畫的時候,事實上都一直從那裡意識到“她事實上就是在平面上面”,一直在那邊操作她的一些物質的條件,所以我覺得她應該挺享受那個物質性跟筆觸、跟她所謂的,從IG上面截取一些圖像。
事實上妳就是在這些「繪畫物質」、「圖庫」、「網路圖庫」之間的這種結構裡面。那我是覺得,這個關係裡面,我剛剛講的那個平面的事實很重要。即便它立起來了,可是那個平面它始終在「圖層」裡面。一般來講我們“作畫”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會考慮到是那個“深度”,因為說到繪畫,如果說立起來的話,可能會有那個深度出現。可是她在作畫的時候,當她擺平的時候—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篩選一些很細目的,麵粉那種—她在繪畫的時候,她一直在篩選。就是一個圖層一個圖層在篩選,然後那個篩選裡面,事實上我覺得就是物質性的。她不是製造深度的幻覺,她就是在那個表層上面。那這個表層我覺得有意思是跟「影像經驗」之間,影像經驗事實上也是一個所謂「圖層」的問題。即便她是擺平的畫,可是她截取的一些所謂這些IG裡面的圖像,事實上也就是一個所謂的「圖層」。
這裡面既然是一個「影像圖層」的話,那麼跟「物質圖層」相遇的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她這裡有意思的是,她的繪畫事實上物質性很強,可是你會覺得她的物質性又跟過去那種繪畫物質性—就是譬如說像她作品裡面,某一部分來講也有一點表現性。那一般來講我們講的「表現性」,都是講給所謂的某一種藝術家的心理深度,或是他想要表現某一種心理內容—可是她的作品裡面的「我」就一直在表層上面演內心戲,並不是透過那種製造以前繪畫的深度的那種東西,而是就在圖層裡面,所有都在圖層裡面,在那一面塗塗抹抹的、遮遮掩掩的。我覺得這一部分的這個圖層關係,跟過去繪畫裡面那種所謂的深度模式不一樣。當然我剛剛提到說,她作品裡面,繪畫到繪畫裝置的這個問題,那是不是對妳來講,是不是叫繪畫裝置,或者說有沒有其他的另外一種命題。我剛剛講繪畫的事實,這個事實本身有沒有可能牽涉到,不只是一個裝置的問題,這個也許等一下可以討論。
大家好,我因為從花蓮過來,萬一狀況不太好的話,可以念那一篇文章(fb發文)。一開始的時候我是說「看就好了。」,事實上繪畫本來就看就好了,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在這邊,還是要說一點東西,所以還是用語言去詮釋。
那因為繪畫本身它的語言,跟我們學的語言當然不一樣,繪畫它本身就是一種語言,不是還要透過語言去詮釋它。我覺得看她的作品其實很直接,就誠如她自己說的「繪畫是一個事實」。從她有一些故意在畫旁邊,做了一個很短的檯座,就是她已經不太區分所謂平面跟立體,她一直告訴我們「繪畫作為一個事實」在那個地方,就跟這些檯座啊,可以看得出來。她的畫雖然有一些掛在牆壁上,但有一些是擺在這些像台座。她一直暗示我們,其實這個空間裡面的這些東西是事實,不是像以前,繪畫住在一個幻覺中、裱框,製造一個幻覺。她作品裡面完全沒有幻覺,就是你在這個地方,你看到的東西,這些材質、物質,還有這些平面給你直接的感受。我想這個就是她作品裡面,我們直接面對的。我們不必要在畫面看到她要說什麼故事,或是她要再現什麼我們曾經看過的東西,她只是全部都給它事實,這一部分,就是她很清楚她在表達這一部分。
因為她作品基本上,我認為是這樣,雖然是2D的,但是它擺在一個空間裡面,事實上所有東西都動員起來了,它就變成不再孤立了。也就是說它不再是內在平面的問題,它變成是整個框,就是它整個環境的「這個」。事實上我當然知道她之前作畫的時候,是擺平了畫,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說她的「視域」很重要,她畫畫不是像以前立起來的,立起來基本上就是製造幻覺,因為立起來就表示,你跟繪畫的關係有一定的距離。然後你會透過視覺去製造一個類似三維的空間,不管那邊是抽象或是空間暗示的,但它就意味著你跟它的關係,就是製造一個「這裡」跟「那裡」的關係。可是她在作畫上面有一點意思的是她「擺平了它」,她在畫的時候,事實上都一直從那裡意識到“她事實上就是在平面上面”,一直在那邊操作她的一些物質的條件,所以我覺得她應該挺享受那個物質性跟筆觸、跟她所謂的,從IG上面截取一些圖像。
事實上妳就是在這些「繪畫物質」、「圖庫」、「網路圖庫」之間的這種結構裡面。那我是覺得,這個關係裡面,我剛剛講的那個平面的事實很重要。即便它立起來了,可是那個平面它始終在「圖層」裡面。一般來講我們“作畫”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會考慮到是那個“深度”,因為說到繪畫,如果說立起來的話,可能會有那個深度出現。可是她在作畫的時候,當她擺平的時候—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篩選一些很細目的,麵粉那種—她在繪畫的時候,她一直在篩選。就是一個圖層一個圖層在篩選,然後那個篩選裡面,事實上我覺得就是物質性的。她不是製造深度的幻覺,她就是在那個表層上面。那這個表層我覺得有意思是跟「影像經驗」之間,影像經驗事實上也是一個所謂「圖層」的問題。即便她是擺平的畫,可是她截取的一些所謂這些IG裡面的圖像,事實上也就是一個所謂的「圖層」。
這裡面既然是一個「影像圖層」的話,那麼跟「物質圖層」相遇的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她這裡有意思的是,她的繪畫事實上物質性很強,可是你會覺得她的物質性又跟過去那種繪畫物質性—就是譬如說像她作品裡面,某一部分來講也有一點表現性。那一般來講我們講的「表現性」,都是講給所謂的某一種藝術家的心理深度,或是他想要表現某一種心理內容—可是她的作品裡面的「我」就一直在表層上面演內心戲,並不是透過那種製造以前繪畫的深度的那種東西,而是就在圖層裡面,所有都在圖層裡面,在那一面塗塗抹抹的、遮遮掩掩的。我覺得這一部分的這個圖層關係,跟過去繪畫裡面那種所謂的深度模式不一樣。當然我剛剛提到說,她作品裡面,繪畫到繪畫裝置的這個問題,那是不是對妳來講,是不是叫繪畫裝置,或者說有沒有其他的另外一種命題。我剛剛講繪畫的事實,這個事實本身有沒有可能牽涉到,不只是一個裝置的問題,這個也許等一下可以討論。
「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個展,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3)
沈裕昌:
那我想是不是我再說一點,就我剛剛提到的「對象」的這個問題,剛剛顧老師有提到就是「場域的」跟「物質的」一個觀點。就是說芝其的畫,我覺得可以注意到,第一個就是說她的畫是平著畫的,不是立著畫的。那當然這個不是一個經驗事實,這個是一個可從跡象上看到的後果。因為我們知道說,繪畫這個東西,它其實是一個「記憶的紀錄」,就是我們做的任何痕跡都會留在上面,而且我們是看著那個痕跡往下想,再繼續留下痕跡的,那個痕跡其實是累加的。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看作品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是所謂一個去時間的空間作品,那其實是一個時間性的作品,只要你理解它的積累的過程的話。所以我們從她的作品上看得出來,這個比較薄透的顏色,然後顏色跟顏色之間混融的方式,它是水分高的,就是說它是很濕的狀態下去處理出來的這樣子的圖像。它沒有什麼滴流,也就是說它是平著畫的,不是立著畫的。那當然立著畫就是會有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對象化」的問題—就是說我跟對象之間是有距離的,而且這個距離可能在古典繪畫裡面會更明顯。不只是出於透視技術,還出於這個繪畫的公共意義,也就是說它要讓更多的人看到,它本來是一個media。當時並沒有這種機械複製的方式,所以它就只有透過增加它的量體,讓更多人可以看到。無論它是透視以前的繪畫,或是透視以後的繪畫,就是這個“立著”的這個圖像,它的目的是為了保持跟大多數人之間的媒介關係,然後它的距離必須是拉遠的,這個完全是「對象化」的。
可是芝其的這個做法,剛剛顧老師提到說她把畫放平,大家可以看到芝其畫的這個尺寸,它沒有大到像行動繪畫一樣,就是人在畫裡面行動,所以她也不是行動,只不過說她的這個畫是平著放的。那你如果在很濕的狀態下,平放之後再立著畫,會有一些滴流的痕跡,這個痕跡就會暗示重力,就是那個顏料跟引力跟重力之間的這個關係。可是芝其的畫裡面沒有這個部分,也就是說其實她在把這個畫放平的時候,除了「不把圖像投射在對立面」的這個意義之外,還包括她在處理圖像的時候,我會覺得比較像是「失重」。我說失重的意思是,她其實在一個很濕的狀態下處理這個顏色之間的混融的時候,她其實是使用這種水性的浮力狀態,去處理這個區塊跟區塊,或者顏色跟顏色的這個關係。當然我不是說她在畫的時候是一個無重的狀態,但是她在概念上其實是失重的,她既是使用了物質的特性,又同時盡量要撤銷掉那種概念上的物質性。
這個也有我剛剛說的,她面對語言的方式,跟她面對物質的方式,我覺得是可以做這個比較。她的作品看單一件跟看一個展,感受上會差蠻多的。我覺得她的作品,嚴格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展。她不是只是做單件單件的作品,然後把它處理成一個展,而是這個展本身可以被視為是一件作品。因為她在理這些圖像的邏輯,首先她需要有一個量,但是在這個量裡面,她又不處理分類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有了一個量,在量裡面處理分類的話,那麼我們就是在把它清晰的概念化;可是如果我要一個巨大的量,我又不處理分類,她面對這個圖像或者說面對材料的方式,其實是數據的,或者說是有資料庫的邏輯,我要有一個量但是我不要清晰,她處理圖像和物質的方式都有這個特點。
然後我想要再多說一小段,她的展名。我一直覺得好奇,因為她用「未力的嘈雜」,這個嘈雜的‘tumult’,後面的這個字‘mult’是「多」、「繁多」的意思,所以「嘈雜」這個字我們是容易理解。但是「未力」的翻譯,她是用‘soft’,就是說軟性的或者說是軟調的。那為什麼會用嘈雜呢,我在這邊想要做一個詮釋,就是說她在處理圖像的時候,她用的是一個「聲音的繁多」的邏輯。如果在這邊我可以稍微提到有閱讀過Michel Serres的人,大概可以想到Michel Serres的「噪音」概念,我覺得能夠呼應這個想法。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她關注的這個“東西”…如果不用“對象”這個字…它的數量是多的,那我們怎麼“面對多”?當然你可以說用這種「範疇」啟蒙理性的方式,我們幫它做分類,所以我們會有圖書館,或者我們會有今天的檢索系統,用檢索系統來面對「多」。可是「多」這個東西,如果是以視覺來說,面對多要產生秩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利用視覺的遮掩效果。因為我們現在面對一群人,可是前面的人會擋住後面,在視覺上會擋住,所以當有這個擋住的關係,它就會產生秩序。這個秩序我們過去就把它稱為「象徵秩序」。就是說「象徵」其實是在建立「秩序」的,而這個秩序是通過遠近邏輯的。當然透視法就是這個意義,所以就是我們通過視覺的遮掩的特質,去拉出一個距離,然後建立秩序。
可是這個是視覺,如果轉換成聽覺的話,這個感官一置換,這個問題、這個方法會失效。因為以聽覺來說,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在睡覺的時候,多小的聲音都構成你失眠的理由。聲音之間,就是在繁多的聲音裡面,任何微小的聲音,不會因為它的量比較小,它就在這個存有裡面不佔一席之地或者被遮掩。所以芝其在面對圖像的時候,我們要把它想像成像在面對一堆噪音一樣,她現在面對一堆圖像,這些圖像之間在概念上,不再有能通過彼此遮掩,或者大小的方式,去建立象徵秩序的這種可能。她在思考的是一種圖像的「象徵秩序」的破壞,在沒有象徵秩序的狀況下,在以前所有能夠處理「多」,在「多」裡面梳理秩序的技術,全部都失效的狀況下,我們怎麼面對這種「圖像的多」?當然我不會說它沒有一種產生意義的方法或者態度,但總之不是以前的這些技術。所以我覺得她之所以用這個「嘈雜」去談她處理的這些圖像,有這個用意在。當然這個就會回應到剛剛顧老師說的影像問題;影像無論你是使用類比或者使用數位,產生的影像它都會有「噪點」。那麼那個噪點,它跟象徵就不一樣,象徵凡存在必合理,可是如果是類比或者是數位的話,它會有噪點,而這個噪點是因為它的中介技術產生的,沒有意義。那我覺得芝其在面對圖像的時候,她其實是用一個噪點的邏輯在面對圖像,而且是通過這種數據資料庫的方式。
那我想是不是我再說一點,就我剛剛提到的「對象」的這個問題,剛剛顧老師有提到就是「場域的」跟「物質的」一個觀點。就是說芝其的畫,我覺得可以注意到,第一個就是說她的畫是平著畫的,不是立著畫的。那當然這個不是一個經驗事實,這個是一個可從跡象上看到的後果。因為我們知道說,繪畫這個東西,它其實是一個「記憶的紀錄」,就是我們做的任何痕跡都會留在上面,而且我們是看著那個痕跡往下想,再繼續留下痕跡的,那個痕跡其實是累加的。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看作品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是所謂一個去時間的空間作品,那其實是一個時間性的作品,只要你理解它的積累的過程的話。所以我們從她的作品上看得出來,這個比較薄透的顏色,然後顏色跟顏色之間混融的方式,它是水分高的,就是說它是很濕的狀態下去處理出來的這樣子的圖像。它沒有什麼滴流,也就是說它是平著畫的,不是立著畫的。那當然立著畫就是會有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對象化」的問題—就是說我跟對象之間是有距離的,而且這個距離可能在古典繪畫裡面會更明顯。不只是出於透視技術,還出於這個繪畫的公共意義,也就是說它要讓更多的人看到,它本來是一個media。當時並沒有這種機械複製的方式,所以它就只有透過增加它的量體,讓更多人可以看到。無論它是透視以前的繪畫,或是透視以後的繪畫,就是這個“立著”的這個圖像,它的目的是為了保持跟大多數人之間的媒介關係,然後它的距離必須是拉遠的,這個完全是「對象化」的。
可是芝其的這個做法,剛剛顧老師提到說她把畫放平,大家可以看到芝其畫的這個尺寸,它沒有大到像行動繪畫一樣,就是人在畫裡面行動,所以她也不是行動,只不過說她的這個畫是平著放的。那你如果在很濕的狀態下,平放之後再立著畫,會有一些滴流的痕跡,這個痕跡就會暗示重力,就是那個顏料跟引力跟重力之間的這個關係。可是芝其的畫裡面沒有這個部分,也就是說其實她在把這個畫放平的時候,除了「不把圖像投射在對立面」的這個意義之外,還包括她在處理圖像的時候,我會覺得比較像是「失重」。我說失重的意思是,她其實在一個很濕的狀態下處理這個顏色之間的混融的時候,她其實是使用這種水性的浮力狀態,去處理這個區塊跟區塊,或者顏色跟顏色的這個關係。當然我不是說她在畫的時候是一個無重的狀態,但是她在概念上其實是失重的,她既是使用了物質的特性,又同時盡量要撤銷掉那種概念上的物質性。
這個也有我剛剛說的,她面對語言的方式,跟她面對物質的方式,我覺得是可以做這個比較。她的作品看單一件跟看一個展,感受上會差蠻多的。我覺得她的作品,嚴格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展。她不是只是做單件單件的作品,然後把它處理成一個展,而是這個展本身可以被視為是一件作品。因為她在理這些圖像的邏輯,首先她需要有一個量,但是在這個量裡面,她又不處理分類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有了一個量,在量裡面處理分類的話,那麼我們就是在把它清晰的概念化;可是如果我要一個巨大的量,我又不處理分類,她面對這個圖像或者說面對材料的方式,其實是數據的,或者說是有資料庫的邏輯,我要有一個量但是我不要清晰,她處理圖像和物質的方式都有這個特點。
然後我想要再多說一小段,她的展名。我一直覺得好奇,因為她用「未力的嘈雜」,這個嘈雜的‘tumult’,後面的這個字‘mult’是「多」、「繁多」的意思,所以「嘈雜」這個字我們是容易理解。但是「未力」的翻譯,她是用‘soft’,就是說軟性的或者說是軟調的。那為什麼會用嘈雜呢,我在這邊想要做一個詮釋,就是說她在處理圖像的時候,她用的是一個「聲音的繁多」的邏輯。如果在這邊我可以稍微提到有閱讀過Michel Serres的人,大概可以想到Michel Serres的「噪音」概念,我覺得能夠呼應這個想法。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她關注的這個“東西”…如果不用“對象”這個字…它的數量是多的,那我們怎麼“面對多”?當然你可以說用這種「範疇」啟蒙理性的方式,我們幫它做分類,所以我們會有圖書館,或者我們會有今天的檢索系統,用檢索系統來面對「多」。可是「多」這個東西,如果是以視覺來說,面對多要產生秩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利用視覺的遮掩效果。因為我們現在面對一群人,可是前面的人會擋住後面,在視覺上會擋住,所以當有這個擋住的關係,它就會產生秩序。這個秩序我們過去就把它稱為「象徵秩序」。就是說「象徵」其實是在建立「秩序」的,而這個秩序是通過遠近邏輯的。當然透視法就是這個意義,所以就是我們通過視覺的遮掩的特質,去拉出一個距離,然後建立秩序。
可是這個是視覺,如果轉換成聽覺的話,這個感官一置換,這個問題、這個方法會失效。因為以聽覺來說,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在睡覺的時候,多小的聲音都構成你失眠的理由。聲音之間,就是在繁多的聲音裡面,任何微小的聲音,不會因為它的量比較小,它就在這個存有裡面不佔一席之地或者被遮掩。所以芝其在面對圖像的時候,我們要把它想像成像在面對一堆噪音一樣,她現在面對一堆圖像,這些圖像之間在概念上,不再有能通過彼此遮掩,或者大小的方式,去建立象徵秩序的這種可能。她在思考的是一種圖像的「象徵秩序」的破壞,在沒有象徵秩序的狀況下,在以前所有能夠處理「多」,在「多」裡面梳理秩序的技術,全部都失效的狀況下,我們怎麼面對這種「圖像的多」?當然我不會說它沒有一種產生意義的方法或者態度,但總之不是以前的這些技術。所以我覺得她之所以用這個「嘈雜」去談她處理的這些圖像,有這個用意在。當然這個就會回應到剛剛顧老師說的影像問題;影像無論你是使用類比或者使用數位,產生的影像它都會有「噪點」。那麼那個噪點,它跟象徵就不一樣,象徵凡存在必合理,可是如果是類比或者是數位的話,它會有噪點,而這個噪點是因為它的中介技術產生的,沒有意義。那我覺得芝其在面對圖像的時候,她其實是用一個噪點的邏輯在面對圖像,而且是通過這種數據資料庫的方式。
顧世勇:
剛剛裕昌老師給我很多訊息出來,剛剛談到「失重」,我在裡面也有提到這個問題,就是說既然是一個圖層,它事實上就是意味著,就是…薄薄的一層…它沒有重力。在一個沒有重力的情況下,“大地”不見了。你在網路上瀏覽裡頭根本沒有大地,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訊息。所以她擺平的,或是所有的東西、物質的這些各種關係,都是不會“沈”的,這個我覺得是她這個時代裡面的語言。那我們講「大地」,是所謂的重的、重力的東西,或是說我們可以立足、著地,但在她的作品上面,這邊沒有立足著地。那這個本身同時就是沒有「在此」,沒有「在此」就是沒有一個“曾經”,就是我裡面提到的「出處」,她的影像沒有“出處”。「出之有處」意思就是有“大地”、“曾經發生過”,你可以看到好像是“曾經看到一個東西”、“曾經在那裡”。然後你會發現那個“在”有一個時間距離,所以會有“靈光”。因為那段時間的距離有一個奇異的時空經驗,就是那段“時間距離”讓我們覺得有靈光,它已經不在了,那就是一種“雖遠猶近”。它很遠可是我們感覺得到那段時間,好像我們現在可以去感受到它。可是在她的作品之中,可能都沒有這個東西,因為沒有大地,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飄在上面的。就像它在圖層裡面,或是在上面,這些圖像的經驗事實上是沒有一個所謂的“經驗”。所有東西都是“經歷”。那「經驗」的話就是要有一個存在的基礎,一個“在此” 居住在一個“大地”上面。如果沒有這個,所有東西都是“經歷”。所有東西就都是不斷地,就像影像不斷地翻閱,就是班雅明談到的“經歷的瞬間”粉碎了“經驗”,粉碎了經驗的光暈。也就是說,把這個經驗的光暈去除了。
那我覺得她的作品正好恰恰是「經歷」,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經歷。那這個「經歷」,剛剛裕昌有提到‘object’,那我會提到‘subject’,就是一個“在什麼之下”,就是說它不是posed在我們前面,‘subject’,就是我們在什麼之下。那也就是說這個很有意思,“我在這些影像訊息之下”,所以她這個subject的情況就跟剛剛你提到的狀況,就是如果要談object跟subject的話,這個很有意思,這個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她作品另外一個有意思是「泛光」,我自己發明的「泛光」,就是說你看到這個作品都好像有某種泛光,泛光不是一種我們在自然光、太陽光下面可以經歷到的東西。而是一種像螢幕、或是像一些過度曝光的這些東西,就是一種泛光,然後泛光就會變成一個問題就是「出之無處」。它是從圖庫裡面—就是裕昌剛剛講到那個「多」,謝謝你剛剛提到那個「多」。圖庫裡面就是「多」的,是不是,「我」無意義,就是「不是獨一無二的」,但靈光是獨一無二的顯現,所以有距離。可是它既然沒有獨一,就會是「多而無一」,沒有一只有多。我覺得它這裡面有意思的是,不是過去那個時代、那個靈光的時代,而是一個泛光的時代。純粹是想像、過度想像,我們不一定要接受,所以說這種「出之無處,多而無一」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她作品裡面很有意思的。
因為所有圖庫這麼「多」,但是事實上這是沒有「單一」的,沒有「出處」,然後也沒有一個“開始”,也沒有“結束”。它作品裡面就是沒有“年代”,沒有“時間”,因為它所有東西都同步。我們如果談「所有東西都同步」的話那就是共時問題,共時問題就是空間問題,她作品裡面沒有時間,所以沒有傷感,因為沒有那段距離。如果只是空間,所有空間、所有圖像的相遇,那就是空間問題。它會回到整個空間的事實。那可以明白它所有東西都在當下,就在你現在這裡發生的東西。所以她會很緊張,如果說我們是坐在這裡,比方說今天覺得會影響到作品,她一定會不舒服,照理說她最好狀況是說,可能就是這些元素一進來的話,所有東西都會動員到她的作品。也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會進入到她的情境裡面,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這是她的框,這是她作品的元素之一,會類似說我們包圍她的作品。所以在這裡就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她的作品最有意思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因為她作品沒有「時間」,所有東西在閱歷中經歷同時都是在那個剎那,然後瞬間即逝,直接變成扁平。所以在扁平的情況下絕對不會有傷感,也不會有疑惑,那我覺得如果是還有一個靈光的時代,還有所謂的「大地」的一種鄉愁的話,那就很海德格式,那就是一個很現代主義的東西。那什麼東西會駐留下來,那當然說這個東西就是取決於你的直觀,妳要回應?
剛剛裕昌老師給我很多訊息出來,剛剛談到「失重」,我在裡面也有提到這個問題,就是說既然是一個圖層,它事實上就是意味著,就是…薄薄的一層…它沒有重力。在一個沒有重力的情況下,“大地”不見了。你在網路上瀏覽裡頭根本沒有大地,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訊息。所以她擺平的,或是所有的東西、物質的這些各種關係,都是不會“沈”的,這個我覺得是她這個時代裡面的語言。那我們講「大地」,是所謂的重的、重力的東西,或是說我們可以立足、著地,但在她的作品上面,這邊沒有立足著地。那這個本身同時就是沒有「在此」,沒有「在此」就是沒有一個“曾經”,就是我裡面提到的「出處」,她的影像沒有“出處”。「出之有處」意思就是有“大地”、“曾經發生過”,你可以看到好像是“曾經看到一個東西”、“曾經在那裡”。然後你會發現那個“在”有一個時間距離,所以會有“靈光”。因為那段時間的距離有一個奇異的時空經驗,就是那段“時間距離”讓我們覺得有靈光,它已經不在了,那就是一種“雖遠猶近”。它很遠可是我們感覺得到那段時間,好像我們現在可以去感受到它。可是在她的作品之中,可能都沒有這個東西,因為沒有大地,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飄在上面的。就像它在圖層裡面,或是在上面,這些圖像的經驗事實上是沒有一個所謂的“經驗”。所有東西都是“經歷”。那「經驗」的話就是要有一個存在的基礎,一個“在此” 居住在一個“大地”上面。如果沒有這個,所有東西都是“經歷”。所有東西就都是不斷地,就像影像不斷地翻閱,就是班雅明談到的“經歷的瞬間”粉碎了“經驗”,粉碎了經驗的光暈。也就是說,把這個經驗的光暈去除了。
那我覺得她的作品正好恰恰是「經歷」,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經歷。那這個「經歷」,剛剛裕昌有提到‘object’,那我會提到‘subject’,就是一個“在什麼之下”,就是說它不是posed在我們前面,‘subject’,就是我們在什麼之下。那也就是說這個很有意思,“我在這些影像訊息之下”,所以她這個subject的情況就跟剛剛你提到的狀況,就是如果要談object跟subject的話,這個很有意思,這個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她作品另外一個有意思是「泛光」,我自己發明的「泛光」,就是說你看到這個作品都好像有某種泛光,泛光不是一種我們在自然光、太陽光下面可以經歷到的東西。而是一種像螢幕、或是像一些過度曝光的這些東西,就是一種泛光,然後泛光就會變成一個問題就是「出之無處」。它是從圖庫裡面—就是裕昌剛剛講到那個「多」,謝謝你剛剛提到那個「多」。圖庫裡面就是「多」的,是不是,「我」無意義,就是「不是獨一無二的」,但靈光是獨一無二的顯現,所以有距離。可是它既然沒有獨一,就會是「多而無一」,沒有一只有多。我覺得它這裡面有意思的是,不是過去那個時代、那個靈光的時代,而是一個泛光的時代。純粹是想像、過度想像,我們不一定要接受,所以說這種「出之無處,多而無一」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她作品裡面很有意思的。
因為所有圖庫這麼「多」,但是事實上這是沒有「單一」的,沒有「出處」,然後也沒有一個“開始”,也沒有“結束”。它作品裡面就是沒有“年代”,沒有“時間”,因為它所有東西都同步。我們如果談「所有東西都同步」的話那就是共時問題,共時問題就是空間問題,她作品裡面沒有時間,所以沒有傷感,因為沒有那段距離。如果只是空間,所有空間、所有圖像的相遇,那就是空間問題。它會回到整個空間的事實。那可以明白它所有東西都在當下,就在你現在這裡發生的東西。所以她會很緊張,如果說我們是坐在這裡,比方說今天覺得會影響到作品,她一定會不舒服,照理說她最好狀況是說,可能就是這些元素一進來的話,所有東西都會動員到她的作品。也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會進入到她的情境裡面,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這是她的框,這是她作品的元素之一,會類似說我們包圍她的作品。所以在這裡就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她的作品最有意思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因為她作品沒有「時間」,所有東西在閱歷中經歷同時都是在那個剎那,然後瞬間即逝,直接變成扁平。所以在扁平的情況下絕對不會有傷感,也不會有疑惑,那我覺得如果是還有一個靈光的時代,還有所謂的「大地」的一種鄉愁的話,那就很海德格式,那就是一個很現代主義的東西。那什麼東西會駐留下來,那當然說這個東西就是取決於你的直觀,妳要回應?
左:顧世勇,沈裕昌,蔡芝其
右:「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個展,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3)
右:「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個展,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3)
蔡芝其:
我怕你們兩個輪來輪去會越來越像天書,資訊量還蠻大的,但有一些在過程中可能會閃現一些想法。然後我覺得可以先從空間或是佈展,比較現實發生的上面去討論好了。就是我一直以來在佈展上都花蠻多時間的,因為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我自己是覺得,在做作品、在單幅的繪畫上,基本上是會讓它「完成」,作品對我來說不是好或壞的那個程度,而是它有沒有「被完成」。可是作品(畫作)要以展覽的形式被呈現的時候,它又會再度的困擾我,因為當它(畫作)走到空間的時候,我就是對它又開始有點沒辦法,因為某一種「完整度」很有可能會被影響,或者說閱讀的方式。反正,我很常在佈展的時候,旁邊的人可能看不懂,因為我一直會拼來拼去、換來換去,然後一直叫工具人,就是幫我放這裡放那裡。可能旁邊的人會覺得,我對於怎麼拼湊這件事情很執著,可是其實我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放。因為我覺得每次放上去的時候,它就不是我覺得是「剛好」的那個狀態,或是我可能沒有辦法用很直接的方式去看到它的完整度。其中還有包括—因為畫布它作為功能性的東西的時候,它的厚度就只是為了支撐那個畫布,或是它(厚度)為了懸掛,所以當它進來空間的時候,那個畫布的厚度突然就變成空間唯一的量體,然後你就覺得很焦慮,就是這個量體,到底是,看了很尷尬。因為平常在畫的時候,其實是忽視那個厚度的,可是當它展示的時候,你就是會注意到那個、那個很重複的量體。然後還有就是繪畫它是矩形的…
顧世勇:等一下,那是因為有重力,你討厭對不對?
蔡芝其:對,就是有那個量體。它作為功能性的時候否定它…
顧世勇:那之前你不是用紙張畫嗎,那為什麼不堅持用紙張畫?
蔡芝其:因為紙張它有一個脆弱感、緊張感,會先介入在作品跟觀眾的閱讀前面。
顧世勇:這緊張不是你要的嗎,你繪畫一直做起來你跟它好像有一點點抵抗,你本身有點叛逆,所以你會覺得就是這樣,跟這個紙張的關係有點緊張,你覺得還滿爽的,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蔡芝其:有,但是那個緊張已經太大聲的話,就會先意識到那個紙的材質。
顧世勇:因為你是保守主義
蔡芝其:對,我可能就是比較那個。反正就是在佈展的時候,就是畫布的這件事情會讓我,就是那量體很煩,就是你平常放在那邊畫的時候~
顧世勇:
但是,因為如果沒有那個量體,你不會呈現那種失重的感覺,它恰恰有意思是這裡。妳如果全部展「紙」的話,那就是它沒有異質性在裡面,它同質性太高了。有一個輕跟重的東西,你用重的東西去凸顯那個輕,這裡面這樣才有意思。就是說我們還看到那個厚度,但是實際上你那個圖形就是很薄,明明都是那麼薄,沒有深度,為什麼始終有個重力在那邊,那剛好是那個重力去凸顯那個圖形的輕。所以我才說你這邊就是「大地」不見,有物理空間那個大地,你咬著那個圖形的時候你會覺得不舒服,對不對
沈裕昌:
其實我覺得妳應該要說,其實妳不是保守,因為妳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雙重否定”,而且不是辯證,(顧:對,它是否定的。)她是雙重否定,因為辯證的意思就是說,我今天有兩個東西,我這個跟那個都不要,但是我要綜合統一成一個,可是她沒有要綜合統一。她全部都不要,可是全部都不要之後她最後要不要有一個,其實她好像也不要。我會覺得她的作品裡面,她在處理物質性的方式也像是這樣,就是她處理的薄,不是在製造薄,她不是在做一個很薄的東西。她其實是在「撤銷」,就是說她做了任何東西之後她就要撤銷,然後留了一個有重力的,有物質性的東西。她撤銷之後,她會留下一些痕跡,然後她通過那個痕跡,她展現的就是那個痕跡。所以我會說,她其實是用一種“去物質的方式在展現物質”。所以應該說,這是我覺得接近芝其的作品,就是說她的談論的方式,包含她創作的方式,就是我會覺得像雙重否定。
然後我稍微回應一下剛剛說的,就是比如說,我們如果今天沒有「辯證」,我們就用這種「雙重否定」的這種方式,從失重開始講。剛剛我們提到說她的作品上面有這個失重的特質,她使用“水”的這種浮力,然後她也不立起來、也不強調她的這種物質性,所以她其實雖然是平放的,可是這個平放沒有回到地面,所以她也不是行動繪畫。她身體的物質性、地的這種引力,在她的處理上都沒有出現出來,那所以妳沒有「重力」、沒有「大地」,當然就是再括號說一下,沒有「死亡」,因此就不會有這個「遠近」。
那沒有這些東西之後,也就是說,妳沒有一個錨定點,沒有錨定點就會造成秩序錯亂,這個沒有錨定點造成的秩序錯亂,就是剛剛顧老師說的:不會有經驗。經驗能夠產生「故事」,就是說我們需要有「經驗」,我們才能夠「敘事」。那芝其的作品,當然她有「圖像」,可是她也“反敘事”,可是她的反敘事又不是現代主義式的
我覺得她在面對「圖像」的方式,她不要敘述,就是說我所謂的,一般我們在說那種“反敘事”的這種作品的意思是說—我讓它從這個故事裡面離開,可是我要讓它以一種“在場”的方式觀看它,就是處理一個“觀看物存在的方式”—可是她也不是這個,她反敘事,可是她也不因此就是直接面對這個對象的存在。所以我覺得她處理圖像特別的地方在這:就是“不敘事,可是也不現象式的處理事物”,這兩個她都不要。就變成說她只能夠處理一些「經歷」,這個經歷我們可以說是數位影像式的,它其實就是一些片段,就是說她的這個圖像,首先沒有“時間”,然後沒有“歷史”,然後我也不說它是“記憶”,可是它是某一種“替代記憶”的東西,然後這個就回到一開始芝其她在瀏覽的這些圖像的方式,她面對一堆社群軟體上的圖像,她不做分類然後不做定調。這些東西其實是在替代每一個人的經驗。那我們區分出兩種“失去經驗”的方式,一種失去經驗的方式,按照班雅明的脈絡就是「戰爭」,或者說是「速度」,就是快速的速度、巨大的噪音,還有戰爭爆炸,然後再來是「電影」,就是第一次電影在人面前就是用那麼快的速度、那麼大的音量出現,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個機械時代帶來的這些衝擊,這個衝擊就會造成「經驗」的斷裂。
可是我覺得芝其在遇到的經驗的斷裂,跟這個力量的斷裂不一樣。她的這種經驗的斷裂比較像是:經驗被置換。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是沒有能力、或者說沒有體力、或者說沒有財力自動去生產經驗,所以我們變成是,面對這些資料庫的圖像,我們需要一個「經驗」的自動生成器,這種「經驗」的自動生成就會變成就只是「經歷」。而且她不去探討她跟經驗之間的關係,不會有經驗,有的就只有經歷的一種,就是短時間的匯聚。這個匯聚我會把它回到她前面說的這個「嘈雜」,就是說她的這種圖像之間以一種噪音的方式聚集起來。當然我們可以再多想一下,噪音它不見得是很吵或者說是負面的、讓你覺得不舒服的,噪音其實意味著「失序的聲音」,就是沒有音色,沒有音量,也沒有節奏,沒有秩序,你在這裡面找不到秩序,可是我覺得妙的是,有一個這樣子的說法,就是人其實是有能力在無秩序裡面努力看出有秩序的,就好比說你只要看到一個對稱的東西,你就會覺得像眼睛,或者說你聽一個無序的噪音,聽久了之後你會以為它好像有序。然後我覺得芝其在這邊,我一樣用剛剛那個雙重否定的邏輯來看,我覺得她在面對圖像的時候,她其實也是在這些嘈雜裡面恍惚看得到一點秩序,但是其實它不是任何秩序。那我想說用這樣的方式去回應她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我怕你們兩個輪來輪去會越來越像天書,資訊量還蠻大的,但有一些在過程中可能會閃現一些想法。然後我覺得可以先從空間或是佈展,比較現實發生的上面去討論好了。就是我一直以來在佈展上都花蠻多時間的,因為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我自己是覺得,在做作品、在單幅的繪畫上,基本上是會讓它「完成」,作品對我來說不是好或壞的那個程度,而是它有沒有「被完成」。可是作品(畫作)要以展覽的形式被呈現的時候,它又會再度的困擾我,因為當它(畫作)走到空間的時候,我就是對它又開始有點沒辦法,因為某一種「完整度」很有可能會被影響,或者說閱讀的方式。反正,我很常在佈展的時候,旁邊的人可能看不懂,因為我一直會拼來拼去、換來換去,然後一直叫工具人,就是幫我放這裡放那裡。可能旁邊的人會覺得,我對於怎麼拼湊這件事情很執著,可是其實我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放。因為我覺得每次放上去的時候,它就不是我覺得是「剛好」的那個狀態,或是我可能沒有辦法用很直接的方式去看到它的完整度。其中還有包括—因為畫布它作為功能性的東西的時候,它的厚度就只是為了支撐那個畫布,或是它(厚度)為了懸掛,所以當它進來空間的時候,那個畫布的厚度突然就變成空間唯一的量體,然後你就覺得很焦慮,就是這個量體,到底是,看了很尷尬。因為平常在畫的時候,其實是忽視那個厚度的,可是當它展示的時候,你就是會注意到那個、那個很重複的量體。然後還有就是繪畫它是矩形的…
顧世勇:等一下,那是因為有重力,你討厭對不對?
蔡芝其:對,就是有那個量體。它作為功能性的時候否定它…
顧世勇:那之前你不是用紙張畫嗎,那為什麼不堅持用紙張畫?
蔡芝其:因為紙張它有一個脆弱感、緊張感,會先介入在作品跟觀眾的閱讀前面。
顧世勇:這緊張不是你要的嗎,你繪畫一直做起來你跟它好像有一點點抵抗,你本身有點叛逆,所以你會覺得就是這樣,跟這個紙張的關係有點緊張,你覺得還滿爽的,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蔡芝其:有,但是那個緊張已經太大聲的話,就會先意識到那個紙的材質。
顧世勇:因為你是保守主義
蔡芝其:對,我可能就是比較那個。反正就是在佈展的時候,就是畫布的這件事情會讓我,就是那量體很煩,就是你平常放在那邊畫的時候~
顧世勇:
但是,因為如果沒有那個量體,你不會呈現那種失重的感覺,它恰恰有意思是這裡。妳如果全部展「紙」的話,那就是它沒有異質性在裡面,它同質性太高了。有一個輕跟重的東西,你用重的東西去凸顯那個輕,這裡面這樣才有意思。就是說我們還看到那個厚度,但是實際上你那個圖形就是很薄,明明都是那麼薄,沒有深度,為什麼始終有個重力在那邊,那剛好是那個重力去凸顯那個圖形的輕。所以我才說你這邊就是「大地」不見,有物理空間那個大地,你咬著那個圖形的時候你會覺得不舒服,對不對
沈裕昌:
其實我覺得妳應該要說,其實妳不是保守,因為妳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雙重否定”,而且不是辯證,(顧:對,它是否定的。)她是雙重否定,因為辯證的意思就是說,我今天有兩個東西,我這個跟那個都不要,但是我要綜合統一成一個,可是她沒有要綜合統一。她全部都不要,可是全部都不要之後她最後要不要有一個,其實她好像也不要。我會覺得她的作品裡面,她在處理物質性的方式也像是這樣,就是她處理的薄,不是在製造薄,她不是在做一個很薄的東西。她其實是在「撤銷」,就是說她做了任何東西之後她就要撤銷,然後留了一個有重力的,有物質性的東西。她撤銷之後,她會留下一些痕跡,然後她通過那個痕跡,她展現的就是那個痕跡。所以我會說,她其實是用一種“去物質的方式在展現物質”。所以應該說,這是我覺得接近芝其的作品,就是說她的談論的方式,包含她創作的方式,就是我會覺得像雙重否定。
然後我稍微回應一下剛剛說的,就是比如說,我們如果今天沒有「辯證」,我們就用這種「雙重否定」的這種方式,從失重開始講。剛剛我們提到說她的作品上面有這個失重的特質,她使用“水”的這種浮力,然後她也不立起來、也不強調她的這種物質性,所以她其實雖然是平放的,可是這個平放沒有回到地面,所以她也不是行動繪畫。她身體的物質性、地的這種引力,在她的處理上都沒有出現出來,那所以妳沒有「重力」、沒有「大地」,當然就是再括號說一下,沒有「死亡」,因此就不會有這個「遠近」。
那沒有這些東西之後,也就是說,妳沒有一個錨定點,沒有錨定點就會造成秩序錯亂,這個沒有錨定點造成的秩序錯亂,就是剛剛顧老師說的:不會有經驗。經驗能夠產生「故事」,就是說我們需要有「經驗」,我們才能夠「敘事」。那芝其的作品,當然她有「圖像」,可是她也“反敘事”,可是她的反敘事又不是現代主義式的
我覺得她在面對「圖像」的方式,她不要敘述,就是說我所謂的,一般我們在說那種“反敘事”的這種作品的意思是說—我讓它從這個故事裡面離開,可是我要讓它以一種“在場”的方式觀看它,就是處理一個“觀看物存在的方式”—可是她也不是這個,她反敘事,可是她也不因此就是直接面對這個對象的存在。所以我覺得她處理圖像特別的地方在這:就是“不敘事,可是也不現象式的處理事物”,這兩個她都不要。就變成說她只能夠處理一些「經歷」,這個經歷我們可以說是數位影像式的,它其實就是一些片段,就是說她的這個圖像,首先沒有“時間”,然後沒有“歷史”,然後我也不說它是“記憶”,可是它是某一種“替代記憶”的東西,然後這個就回到一開始芝其她在瀏覽的這些圖像的方式,她面對一堆社群軟體上的圖像,她不做分類然後不做定調。這些東西其實是在替代每一個人的經驗。那我們區分出兩種“失去經驗”的方式,一種失去經驗的方式,按照班雅明的脈絡就是「戰爭」,或者說是「速度」,就是快速的速度、巨大的噪音,還有戰爭爆炸,然後再來是「電影」,就是第一次電影在人面前就是用那麼快的速度、那麼大的音量出現,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個機械時代帶來的這些衝擊,這個衝擊就會造成「經驗」的斷裂。
可是我覺得芝其在遇到的經驗的斷裂,跟這個力量的斷裂不一樣。她的這種經驗的斷裂比較像是:經驗被置換。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是沒有能力、或者說沒有體力、或者說沒有財力自動去生產經驗,所以我們變成是,面對這些資料庫的圖像,我們需要一個「經驗」的自動生成器,這種「經驗」的自動生成就會變成就只是「經歷」。而且她不去探討她跟經驗之間的關係,不會有經驗,有的就只有經歷的一種,就是短時間的匯聚。這個匯聚我會把它回到她前面說的這個「嘈雜」,就是說她的這種圖像之間以一種噪音的方式聚集起來。當然我們可以再多想一下,噪音它不見得是很吵或者說是負面的、讓你覺得不舒服的,噪音其實意味著「失序的聲音」,就是沒有音色,沒有音量,也沒有節奏,沒有秩序,你在這裡面找不到秩序,可是我覺得妙的是,有一個這樣子的說法,就是人其實是有能力在無秩序裡面努力看出有秩序的,就好比說你只要看到一個對稱的東西,你就會覺得像眼睛,或者說你聽一個無序的噪音,聽久了之後你會以為它好像有序。然後我覺得芝其在這邊,我一樣用剛剛那個雙重否定的邏輯來看,我覺得她在面對圖像的時候,她其實也是在這些嘈雜裡面恍惚看得到一點秩序,但是其實它不是任何秩序。那我想說用這樣的方式去回應她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左:Tsai Chih-Chi 蔡芝其 soft_tumult_p03, 2022, Acrylic on canvas 壓克力顏料、畫布, 72.5×53.0cm
右:「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個展,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3)
右:「未力的嘈雜 」 蔡芝其個展,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soft tumult' Tsai Chih-Chi Solo Exhibition,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Taipei (2023)
沈裕昌:
最後我想再談兩個東西,然後第一個就是說,我剛提到的這個「無限鏡像」。我把芝其她的作品,看成是這個無限鏡像裡面的一種切片,我們看她的創作,她塗的方式就是薄,而且這個布的紋理跟質地其實是裸露的,裸露在這個透明的顏料層下面,能夠看得到的。然後呢,這個畫布其實也有比較大面積的「留白」,這個留白它又像是這個牆往這個畫布裡面的延伸。回到我們在這個討論一開始的時候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物質性的東西是出現的,比如說像這種檯座、或者說是這種框、然後還有就是打光的時候,我們依然可以特別意識的到這個白的畫布,在白牆上有的這一種“厚度”的這個差距,這個其實是我們一直看的到,那還包括說,她比較濕的這種用筆的方式,跟一個音韻模糊的一些輪廓。綜合這一些呢,我剛剛有提到,我覺得芝其的這種處理畫的方式,她一樣關注顏料而且也關注它的物質性,可是她希望顏料能夠以最物質性的方式,消去它的物質性存在,但是她用的方式其實又不是這種欺瞞技法,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這,我們可以看得到這種思考顏料的歷史,從這種欺瞞技法,把這個顏料變成寫實物像,去撤銷掉顏料自身,這是古典的做法,或者說現代的做法讓顏料以物質自身的方式出現。可是芝其的做法不是前兩者。
就是說她又要顏料撤銷掉它的物質性,可是她又沒有回到這種“欺瞞技法”,那麼所以她的做法是什麼,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她的顏料處理得非常的薄,然後讓這個底材幾乎是裸露的,所以看起來又像是一種被刮掉的這個痕跡,又像是投上去的這種光暈,就是用剛剛顧老師說的「泛光」,然後我對「泛光」的物質性理解,就是說畫面上既可以看到這些,看起來像是被抹掉的痕跡,又可以看到一些像投影的這種光暈,所以從抹掉的物質痕跡到投影的光暈之間,我覺得在這裡面有一種就是辯證的非物質性,當然非物質性它仍然是物質性,只是它是一種對物質性的否定。
顧世勇:
這個蠻有意思的。也就是說她作品物質性很重要,可是並不是強調那個物質,她恰恰是用物質性否定物質。因為她感覺很像從媒材性轉向媒體性,就是說有媒材性,可是她同時,因為你會覺得又不是那麼媒材性,你剛剛提到的是用媒材否定媒材,因為之所以能否定媒材,是因為它帶有媒體性,就是「媒介」,它變成一個媒介,所以說以前的顏料或者是物質性的東西,你會發現說這些顏料都是為了…如果從「再現」的角度來講,讓你忘記顏料,譬如說畫了一盆花,讓你忘記那個顏料,而是像一盆花,或者說回到物質主義就是說,它都沒有再現一盆花,它只再現它自己,就是說顏料就是它自己而已,那就像印象派那個莫內的荷花,你近看,那個肌理,都看到顏料的這個底,這就是物質性本身。就是說它既不是過去那種顏料,它為了對象「再現」,我忘記顏料,然後發展到這個印象派的時候,顏料本身不再為誰服務了,它為它自己,所以它有物質性。可是現在芝其很有意思,她有物質性,可是她物質性不是要強調那個顏料本身,就是說有啊有物質啊,可是怎麼感覺上好像有一點點怪怪的,這個怪怪就是它有影像感,所以你透過某一種影像感去否定那個物質性,所以從媒材性轉向媒體性。那就是,她作品裡面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媒介”,她作品的始終跟媒介有關。還有的時候,她的東西我剛剛提到說,跟我們所有人佔據所有空間的事實都一樣,它不是“再現”的,不是“敘事”,就是說譬如說你現在看到她每一張畫,事實上跟旁邊的這些“防火”…或者是“把手”都一樣具體,一樣是一個事實本身。那這事實互相干擾,所以她不會把它視為說,它是可用的,這邊是不可用的,她把它視為是一個事實。那也就是說某一部分來講,她帶有某一種“現象還原”。就是說把所有東西都還原到一個你直接跟她面對的,你不用去對它有一個過去你對這個把手的理解,對門的理解,全部放入括弧,人家的畫都放出括弧,是否是裡面的事實,你正在經歷這個事實。所以你在這邊,譬如說對我來講,所有東西這個事實都在現場,所以你才會很緊張所有東西都是事實。是不是。
蔡芝其:是,但也沒有很緊張啦
顧世勇:不是很緊張,也不用那麼緊張,就是說「在意」,好不好
蔡芝其:因為剛剛老師講到空間,應該說包含打光吧,我自己的用詞是說還原這個空間的現實,把展示空間還給現實空間,因為就是接續到我剛剛講繪畫展示的陳列,如果是比較齊平並列的,或是在一個視覺水平齊高的狀態下,我覺得那樣的話,畫面的外框會有一種暗示,就是引導我們去看到的是畫內所建構的那個深度…所以為了排除這個路徑,我想要讓它那個厚度的物質性,可能在空間跟它的空間現實是和諧的…我想我會做一些小的台座,可是我也沒有很在意這個台座到底要是什麼樣子,反正就是在空間裡面創造一些肌理,或是說它到底是現實空間,還是它只是一個展示空間,就會想是讓它變成是一個感覺開啟的整體空間…就是都是現成物的調度。因為作品的單幅也不是一個具有中心或是有故事性的人物,因為它可能就是一個單位,或是一個元素的人或組合,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然後回應老師剛剛講的。
最後我想再談兩個東西,然後第一個就是說,我剛提到的這個「無限鏡像」。我把芝其她的作品,看成是這個無限鏡像裡面的一種切片,我們看她的創作,她塗的方式就是薄,而且這個布的紋理跟質地其實是裸露的,裸露在這個透明的顏料層下面,能夠看得到的。然後呢,這個畫布其實也有比較大面積的「留白」,這個留白它又像是這個牆往這個畫布裡面的延伸。回到我們在這個討論一開始的時候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物質性的東西是出現的,比如說像這種檯座、或者說是這種框、然後還有就是打光的時候,我們依然可以特別意識的到這個白的畫布,在白牆上有的這一種“厚度”的這個差距,這個其實是我們一直看的到,那還包括說,她比較濕的這種用筆的方式,跟一個音韻模糊的一些輪廓。綜合這一些呢,我剛剛有提到,我覺得芝其的這種處理畫的方式,她一樣關注顏料而且也關注它的物質性,可是她希望顏料能夠以最物質性的方式,消去它的物質性存在,但是她用的方式其實又不是這種欺瞞技法,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這,我們可以看得到這種思考顏料的歷史,從這種欺瞞技法,把這個顏料變成寫實物像,去撤銷掉顏料自身,這是古典的做法,或者說現代的做法讓顏料以物質自身的方式出現。可是芝其的做法不是前兩者。
就是說她又要顏料撤銷掉它的物質性,可是她又沒有回到這種“欺瞞技法”,那麼所以她的做法是什麼,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她的顏料處理得非常的薄,然後讓這個底材幾乎是裸露的,所以看起來又像是一種被刮掉的這個痕跡,又像是投上去的這種光暈,就是用剛剛顧老師說的「泛光」,然後我對「泛光」的物質性理解,就是說畫面上既可以看到這些,看起來像是被抹掉的痕跡,又可以看到一些像投影的這種光暈,所以從抹掉的物質痕跡到投影的光暈之間,我覺得在這裡面有一種就是辯證的非物質性,當然非物質性它仍然是物質性,只是它是一種對物質性的否定。
顧世勇:
這個蠻有意思的。也就是說她作品物質性很重要,可是並不是強調那個物質,她恰恰是用物質性否定物質。因為她感覺很像從媒材性轉向媒體性,就是說有媒材性,可是她同時,因為你會覺得又不是那麼媒材性,你剛剛提到的是用媒材否定媒材,因為之所以能否定媒材,是因為它帶有媒體性,就是「媒介」,它變成一個媒介,所以說以前的顏料或者是物質性的東西,你會發現說這些顏料都是為了…如果從「再現」的角度來講,讓你忘記顏料,譬如說畫了一盆花,讓你忘記那個顏料,而是像一盆花,或者說回到物質主義就是說,它都沒有再現一盆花,它只再現它自己,就是說顏料就是它自己而已,那就像印象派那個莫內的荷花,你近看,那個肌理,都看到顏料的這個底,這就是物質性本身。就是說它既不是過去那種顏料,它為了對象「再現」,我忘記顏料,然後發展到這個印象派的時候,顏料本身不再為誰服務了,它為它自己,所以它有物質性。可是現在芝其很有意思,她有物質性,可是她物質性不是要強調那個顏料本身,就是說有啊有物質啊,可是怎麼感覺上好像有一點點怪怪的,這個怪怪就是它有影像感,所以你透過某一種影像感去否定那個物質性,所以從媒材性轉向媒體性。那就是,她作品裡面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媒介”,她作品的始終跟媒介有關。還有的時候,她的東西我剛剛提到說,跟我們所有人佔據所有空間的事實都一樣,它不是“再現”的,不是“敘事”,就是說譬如說你現在看到她每一張畫,事實上跟旁邊的這些“防火”…或者是“把手”都一樣具體,一樣是一個事實本身。那這事實互相干擾,所以她不會把它視為說,它是可用的,這邊是不可用的,她把它視為是一個事實。那也就是說某一部分來講,她帶有某一種“現象還原”。就是說把所有東西都還原到一個你直接跟她面對的,你不用去對它有一個過去你對這個把手的理解,對門的理解,全部放入括弧,人家的畫都放出括弧,是否是裡面的事實,你正在經歷這個事實。所以你在這邊,譬如說對我來講,所有東西這個事實都在現場,所以你才會很緊張所有東西都是事實。是不是。
蔡芝其:是,但也沒有很緊張啦
顧世勇:不是很緊張,也不用那麼緊張,就是說「在意」,好不好
蔡芝其:因為剛剛老師講到空間,應該說包含打光吧,我自己的用詞是說還原這個空間的現實,把展示空間還給現實空間,因為就是接續到我剛剛講繪畫展示的陳列,如果是比較齊平並列的,或是在一個視覺水平齊高的狀態下,我覺得那樣的話,畫面的外框會有一種暗示,就是引導我們去看到的是畫內所建構的那個深度…所以為了排除這個路徑,我想要讓它那個厚度的物質性,可能在空間跟它的空間現實是和諧的…我想我會做一些小的台座,可是我也沒有很在意這個台座到底要是什麼樣子,反正就是在空間裡面創造一些肌理,或是說它到底是現實空間,還是它只是一個展示空間,就會想是讓它變成是一個感覺開啟的整體空間…就是都是現成物的調度。因為作品的單幅也不是一個具有中心或是有故事性的人物,因為它可能就是一個單位,或是一個元素的人或組合,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然後回應老師剛剛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