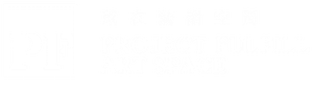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陳松志:無法專心的煙」展覽座談紀實
2018/ 05/ 19
引言人:林珮鈺(就在藝術空間總監)
與談人:黃建宏(策展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所長)
陳松志(藝術家)
林珮鈺:哈囉大家好!謝謝你們抽空過來參加這次展覽座談會,我是就在藝術空間的總監林珮鈺,這次展覽其實是安排在就在藝術十週年計畫裡面的第二個部分。這次就在藝術十週年計畫特別邀請黃建宏老師來策劃。在二月份,已舉辦過第一檔的是土耳其藝術家哈廷.奧倫利(Fahrettin Örenli)的個展,這一次進行到第二個部分。這一次就是由我們自己的代理藝術家陳松志,這已經是這位藝術家與就在第五回的合作個展,這次展覽又會和這個空間產生什麼火花,我們今天就直接進入主題,特別邀請策展人和藝術家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黃建宏:我在想讓藝術家充分的表達他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先稍微來做一下襯底的工作,也就是說到底可以在什麼樣的故事背景底下來了解?或者說來感受松志的作品,我在想就是剛剛珮鈺已經有說到起因於十週年的一個策畫。在第一檔展覽,我跟珮鈺談及,我要找一個藝術家是在台灣大家都不熟悉,然後她自己也不認識,就是要找這樣一個藝術家來證明這個畫廊的實力,因此就找了一位土耳其藝術家哈廷.奧倫利。然後在第二檔展覽就是目前的陳松志,以及第三檔展覽的周育正。當初有這樣一個思考在於這三檔展覽其實有三種藝術家,一個藝術家是珮鈺完全陌生的,那就是試她的膽量。然後會有一檔展覽就是她長期合作的藝術家,也就是她持續經紀的藝術家展現的是就在的累積以及藝術家的突破。然後再有一檔展覽是她有合作過但是沒有經紀的藝術家,這點要試試「就在」的開放程度。我們會知道對於一個空間的經營者來說,其實面對這三種藝術家其實那個心情跟狀態其實都會是不一樣的,甚至在處理空間以及作品上其實都不一樣。那這三檔之中又特別是松志這一檔,最初是要請他要做一個空間,這空間是要做什麼?其實珮鈺在六月初的時候,她會邀請其在亞洲同樣是當代藝術空間的經營者一起來跟她對話,也就是他們要去交流到底像這樣一個中型藝術機構,或者甚至中小型的畫廊在今天的亞洲是有可能可如何運作?所以松志他原本,他其實最初我們在跟他協商或者說在跟討論合作的時候,就是希望他做出一個開放空間,這個空間是我們要在這裡面要去激發一些想像。那周育正的部分其實他就是可以進來這個空間,然後如何營造一個機會是可以跟其他藝術家合作,所以這個我就先不爆梗,後續你們接續到第三檔展覽的時候就可以過來看一下藝術家會怎麼來處理。那回到今天的主題,在這裡我覺得稍微再講一下這個空間,你們可以感覺到這裡其實就是一個辦公室,辦公室感覺上是一個非常功能性的地方,可是這辦公室其實是珮鈺她一剛開始,也就是當時有四個人要一起去做跟藝術有關的理想,然後在想一些新的路子,一剛開始在網路上面去做,最後進行到這個實體空間,以及她們開始意識到似乎要做一個實體空間來經營的這件事情,這四個人在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大的桌子曾經是一起工作著的。到最後卻只剩珮鈺一個人在這裡持續下來?我想這裡面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座談今天就乾脆進到她的辦公室來談,這是有意思的!因為我在想所有的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者說你在開始個人生涯的時候總會有一個地方可能是對你來講是重要的,然後它同時也陪伴著在這裏面發生所有的事情,因此我覺得大家今天的對話或許就應該在這裡,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還有一個「轉折」就可以開始今天的對話。這個「轉折」話說這在一剛開始也是未知的!因為假設有一個狀況,你原本找一個建築師或者室內設計師跟他說:「誒你幫我們來設計一個空間或幫我們來創造一個空間」。然後我們就找到松志,然後當這個人做完空間他把空間裝設好了之後,他就告訴你,你將不能在這裡做任何事情,必須要尊循我的創作。大概在松志之前,我只知道一個人這麼幹的就是安藤忠雄!他蓋好了美術館然後去確立的這個廳要放什麼作品,他簽了約說五年不能動,甚至椅子都是他選的,也表示五年不能動。還好松志沒有像安藤忠雄那麼殘酷!也就是那個空間狀態在完成後的五年都將不能改變。所以我在想其實像這樣的合作,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既然今天松志面對的是一個空間,那我覺得因為我們就是在藝術裡面在談論這件事情或來思考這件事情或感受這件事情的話,我覺得有一個最基本及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最難的事情,就是怎麼樣讓空間變成是未知的。其實這件事情非常難,因為其實大家現在都很厲害,我相信處在這空間裡面,很多人其實都很敏銳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每個人進到一個空間到底要做什麼事或要幹嘛其實都非常清楚!其實今天很少人還會進到一個空間然後他會感覺到害怕,或者他可能覺得陌生。你會發現我們可以來進行一個旅遊的規劃,也就是說我怎麼樣在這個旅程中面對的全部都將是我陌生的空間環境,譬如我今天要去京都玩然後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地方,但其實你會發現今天的你,即使你以前從來沒有去過,可是京都的空間其實已都是你可以想像的。甚至這些城市環境他們幫你規劃的很好,也就是說當你到一個新的城市其實所有的空間其實都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從來沒有來過。所以我在想松志或許帶給我們一個最寶貴的經驗,應該是他如何讓這個空間是未知的!那個未知並不是你沒去過或者是你沒看過他的照片或者是怎麼樣,而是到底那個感覺怎麼樣被創造出來!所以接下來我先丟出這個東西然後待會我可以再多說一點,我們就先讓松志說一下。
陳松志:謝謝建宏老師,謝謝大家今天下午來這個地方參與我們的座談,關於剛建宏老師提到的部分,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早就理解到這應該會是一個要能提供「人」與「事」可能可以參與其中,可能可以在裡頭有很多事件的空間調性。對我來講我覺得那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恐懼的本身,就像我的英文展覽名稱A Fork in the Road,它其實都是一個選擇,你選擇了這條路,必然要放棄另一條路,因為你只能走在一條路上。或者你可能要倒頭回來再去走另外一條路。因此我在思考這個展覽的時候,其實在面對的是一個我很熟悉的空間,也因為過度熟悉了,其實你知道這空間裡頭有非常多的細節你不能迴避它!那對我來講,既然這麼的熟悉,但是它突然、頓時之間讓我少了某一種發現的趣味在這裏頭。於是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該怎麼樣去燃起在這個空間當中的最陌生的感覺,所以我就開始回應到那個陌生,其實我覺得陌生只有一種狀況就是當你在看不清楚的狀況,你就會對這個空間產生陌生感,因此對我來講或許這一次的展覽在展覽的作品呈現以及思考,我其實選擇了的是一個滿封閉的系統,所謂封閉系統就是我希望讓這個結構系統它是被遮蔽起來,包括這個空間它可能被地毯覆蓋了、被一些織品等總總的東西覆蓋了。因為覆蓋了這些東西讓你看不到了,你產生了更多的未知,或者更多的對於這個空間的延伸。事實上「就在」的空間並不大,但它卻有很多很零碎的格局,因為這個空間它本來就不是作為一個展場來使用,它原本建築就是一般的住宅的類型,那對我來講我如何在這個有所局限的範圍裏頭,讓這些阻礙讓觀眾因看不清楚而產生延伸。所以那回到一點就是,究竟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最後選擇一條路是回到一個最沒有聲音的地方。所謂沒有聲音,雖然你聽到這裡面有很多干擾的聲響,可是你可以選擇去聽或不去聽,或者你根本就聽不到!所以我覺得這個封閉的系統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我這一次的選擇,它可能不見得是我們講二元看待正面或是負面的,它就只是個選擇!所以嚴格來講,我其實覺得這個對於跟我合作的人反而其實是最辛苦的,也就是多數的時候我在做是事情的本身其實是容易的,但是在抉擇或者是在排拒誘導的過程是最困難的。因此這次最後你看到這個展覽表現出來的樣態其實很零散的,它其實沒有要說一件很明確的事情,也就像你從中英文字義上,中文字義的煙,它可能聯想到就是菸草,但它也可能是煙灰總總的……,它其實有太多開放的可能,作品本身其實即在探討那個抉擇跟擾亂的狀態。其實我覺得把這些人、事件移放到這個空間裡頭,在這裏發生的事物對這個作品本身其實也是個擾亂,那就是整個狀況有點反客為主,或者是這裏頭其實有一個迫使我們必須去做某種選擇跟決定這件事情。但我相信這個過程都是好的,也就是說我們人得要先面對問題,才有辦法穿越問題的本身,不然其實你就是被擋在這個表層之外,我大概先補充到這裡。
黃建宏:好。我再接下來講一些事,也就是先預告一件事情,就是你們會發現其實這個展覽到目前並沒有策展論述,因為其實策展論述都還在過程的進行之中,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合作的策展人然後我期待藝術家其實在給我一個我想像不到的空間,因為我覺得今天策展人的角色究竟是什麼?如果策展人的角色就是一個全知者好了,也就是說他已經很清楚這個藝術家是要幹嘛,然後他已經預知這個藝術家的作品,其實這樣的一個策展人除了做生意他還有什麼好做的。或是說除了做典禮之外還有做生意之外,其實也就沒有什麼好做的。因此我還是會期待松志他到底可以帶給我或我們什麼樣的表述空間?既然這樣的話,其實策展論述就不可能在作品展覽還沒發生完成這之前就寫完,所以既然松志他要處理空間,然後其實對於整個展覽來講的話,展覽裡面到底存在多少種空間其實論述本身他也是一個影響空間的事情,所以我其實會採取一種方式,假設他是一個料理空間的廚師好了,然後我將會定期來這邊感受這個空間,之後我會發表一些對空間的想法,我會錄音下來然後把這個當作食材交給他,然後因為這些東西這些材料他其實都是策展人自己講的嘛,然後可以是讓藝術家他試著從這些材料裡面去完成出一篇論述,就是說他不能自己寫自己的話,他要寫我的話可是是由他來寫,所以我也很期待到時候會不會寫出來一篇論述是我看不懂的,是我不認識的,我也在期待這樣的事情,因此在這個展覽的規劃裡面,其實會在很多的層次我都希望藉著松志的敏感度,了解藝術家對我們來講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們如果說比較功利一點的講,藝術家到底對我們有什麼用處,當然我如果有錢可以收藏跟進行買賣的話,那當然藝術家就可以提供我作品就會有某種投資的用處。可是我並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才要靠講話維生,也就是說我自己其實會這樣覺得,藝術家對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可以提供給我們感受不到的感覺,這個就是我覺得藝術家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提供這些感性的層次,甚至我如果跳得快一點,對我來講感性的層次越多,我們的這個世界或者我們的整個社會民主化程度的可能性就會越高。因為感受多才會讓人有想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連結,我不認為感受非常貧乏的人,他的思想會有趣,然後他的思想會真的有創意。所以這個也是我在這樣的一個機會裡面,我一直在期待松志這邊他能夠跟我產生什麼樣的交流跟互動,那我在這邊在帶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我覺得因為大家也都有看過那個空間,或者說去感受那個空間,我在想大家在感受過以後然後就走過來裏邊,然後我們開始來談這件事情其實是還滿有趣的。我覺得我先講松志的,就是說我自己整理出來松志的某種操作作品的思考方式,我個人覺得日常的感覺對松志來講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一個人在他的日常裡面到底感受到什麼?他到底覺得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底下、處境底下其實非常關鍵。然後松志他會把這樣一個日常處境裡的東西,不是直接把它再現出來,有很多的藝術家在他在感受到一些日常片段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藝術家處理的就是去放大那個瞬間,放大瞬間大部分都用錄像,要不然就是去放大那質地、質感,那可能會透過攝影或透過一些物件的呈現或堆積。這些藝術家其實他們在面對日常生活或日常性的時候,絕大部份都是在思考怎麼樣用放大的方式再現它。可是在松志的創作之中,其實我從來沒有跟他講過這樣的事,也就是說他是把日常所感受到的事情,他會去找到一些材料,並去設計一個工作的過程,我覺得他好像一直有一個偏執,這個偏執就是他一直要把日常的那個根本就非常難以具體化的東西,他要透過一個操作的過程讓它附著或黏著在那個材料上面。然後再把那個材料放回空間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他會讓你夾雜在好像一個「裂縫」之間的感覺,也就是說一方面你可以知道有日常的東西,可是另外一方面你會覺得他好像有一種非常偏執純化的過程。也就是說這兩種東西其實我覺得是在看松志大部分的創作裡面會讓人家感受到的展現,我會覺得這個感受是一個有意思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裡面,除非你對於你生活的控制能力可以到非常的高,要不然的話,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活在這樣的一個混雜性裡面,可是在這個混雜性裡面對於松志來講他並不是倚賴一個非常直接的呈現,而是它有一個操作過程,我會覺得所以我們在看松志的作品的時候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層次,我覺得大部分的層次或許都可以比較清楚,但我覺得他對待材料操作的那個偏執所帶有的情感,其實是跟藝術家本身應該是最為非常靠近的事情。我都一直沒有談到這個展場,於是我就大概先丟出我對松志他在進行創作的時候的操作思考,然後我們來聽聽看松志怎麼講。
陳松志:好!其實建宏老師有提到這次滿特別的像是回到一個作展覽跟做創作的過程,一直以來其實我們常談到創作中的獨立性也就是創作行為中的獨立思考。創作本身其實就要能夠充分發揮的的獨立、獨特精神,也就是過程之中要能思考到任何的創作都會跟他者產生關係,但對我來講有時候跟人在互動上那溝通的本身,對我來講就是一種是一個還蠻難進行的一個抉擇以及過程。因為有時候當下決定了這件事情其實我後來很快的就反悔了,這其實包含了一個允諾的過程,所以對我來講我歷年的創作裡,當初十週年計畫的三個部分裡頭,建宏老師跟珮鈺這邊也思考到,好像要把我跟其他的藝術家搭配在一起做一個組合確實是一個滿困難的事情。因為好像那個東西是你把他(它)放在那個位置裡頭但他(它)好像又變成了不屬於自己了,他(它)可能會被依附在另外一個或是消失在另外一個他者的內裏裡頭了,所以我覺得這裡頭回到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一個個人秀了。所以我覺得建宏老師在這裡也提供給我一個非常充分的空間,以致後來我在思考到這一次的整個展覽的節奏裡頭,建宏老師丟出了一個後論述這件事情,因為其實老實講,我要做什麼其實似乎連我自己,都有可能在製做的這個當下可能還在(會)改變。其實沒有太多人能夠知道到底我要做什麼,所以那這裡回到一點就是信任的問題,回到是一個人根本裡頭,你對於這件事情的信任。我真的覺得我非常的幸運我有一個很信任我的畫廊主,有很信任我的策展人,這是一個蠻複雜卻難得的經歷,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也讓我在這裡頭很充分的讓我有多一點的時間來讓這東西就像一個濾化、沈澱的過程一樣。所以當我先有作品,做完之後我們這次的策展我們一開始在對外的訊息裡頭,其實我們丟出的不是策展人的論述,而是藝術家的自述,這個回到以前的個展當然也就是這樣,但這次一樣的,讓我以我自己的自述,那其實是對我來講,先有作品完成之後,這份自述文字是另一種再創作,因為我必須要用文字的系統、語言的系統、表述的系統來釐清我自己的琳琳總總。這是一個從開始進行到凝視個人創作的部分。以致到後續這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觀眾在這裡頭總總的參與,讓我們彼此有更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也在後續才會產生建宏老師在作品裡頭持續的、多一點的展覽細節內容分享。我剛想到這個東西好像是很有趣有點,像是你們在展場裡頭看到最大面積的活性碳原粒,活性碳粒它原本的素材其實來自於植物的有機狀體,那好比就像我創作出來的東西,慢慢地經由一個策展的系統,他者論述的系統慢慢地經過一個濾化的手續最後被呈現出來。我覺得那一個最清晰的處理,它讓彼此都充分表達,然後就形成的總體成為我們樂見看到的。它保留了策展人的言說,同時也讓藝術創作者在這裡頭能夠選擇創作中封閉的部分或有願意開放出來的部分可以進行適時、適應的表達。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蠻特殊的一個展覽製作與跟策展進行。
黃建宏: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展場裡面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對這些事情的想像,以及對松志創作的一個想像。對我來講因為我自己以前是學化學的,所以其實學化學相較於其他的學科,或許會多有一種奇特的想像力,來自於對於所謂分子的世界,總會有一些特別的幻象。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必須背很多的分子式,然後我們還要背元素表,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本來就有非常多的粒子,因此大家也都會說現在世界是原子化的世界,然後有非常多分子。包含我們以前在買藥的時候會去表述出上面的成分,基本上在廣告的時候更會表達出內容的成分細節,這大部分都還是一個非常類比世界的思考表達。比方說這個藥品是來自什麼植物或是來自於什麼,也就是說那都還是存有一個外在型態的表達。可是你會發現現在大家在談論營養食品或者藥品的時候,其實大家可以對這些分子式的學名都朗朗上口,其實我們的世界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其實在發現影響我們的東西越來越是在那些看不見的分子,也就是大家被說服了!而且大家現在開始跟學化學的人一樣有一種幻想的能力了。也就是說你為什麼會覺得你去吃一種叫做某某化學式的東西,然後你就覺得你的身體改善了,其實這是需要靠非常巨大的想像力。這次松志其實他選了一個很有趣的材料,因為如果我們就這次展覽裡面,松志選了不同層次的素材,然後我會覺得這些材料都是非常的有趣。很多的藝術家在選材料的時候,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大部分的藝術家在選素材,當然我們很多都是處理視覺的,所以在一剛開始選擇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會根據它的質地、它的紋理、它的型態都會有關,因為這個跟我們的視覺其實是非常直接聯繫的。接下來我們因為在教科書上學了、看到了杜象(Marcel Duchamp),當然我們很少看到杜象的原作,大概都是看到他作品的圖片,於是我們就會開始去想像工業製品它在一個文化上面跟我們人產生了關係,所以開始有這一個層次我們為什麼會選這個材料?其實會有存在這樣邏輯層次思考的關聯。然後接下來當這個世界很多都在討論檔案的時候,甚至在討論所謂的證物美學,就開始將所有的物都依附在一個歷史的脈絡底下,開始去尋找這個來歷。從十年前開始可能就會有一些搞植物的藝術家,譬如說特別是香菇的培育或是說黴菌的培育,大概在十年前在巴黎東京宮就曾做過這樣的展覽。也就是開始當我們在對空氣裡面的味道,我們開始是用粒子去想像他,這感覺上好像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些想法,可是到底人如何把這個想像真的具體的呈現與相信,其實這需要很長的時間。我覺得這一次很有趣的是松志他選擇了活性碳,如果你從今天的日常生活裡面你會發現,現在有越來越多人他會告訴我們各式各樣的知識,怎麼樣的東西它會產生什麼作用,這些作用其實可能會對人造成有害或對人產生幫助。所以我們如果說藝術家他並不只是帶給我們視覺上的東西,而是他必須要開放或者必須要在創作上能擴張我們的感性。那很能看出松志這次他選用了活性碳其實他裡面有一個滿有意思的角度,並不是說松志讓我們看到的粒子,我想松志沒有這種魔力,他可以讓我們看到空氣裡面的分子,可是他開始試著在選取一種材料,也就是說你會看到大部分他所選取的材料不管是活性碳、地毯、或是他是自己穿過很久的布鞋或皮鞋,還有那些被油墨重新刷過的報紙,最後塞進去鞋子裡面。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事情,這些材料的共通性是什麼?它們都有吸收性,所以其實我們到底要如何讓這種吸收的狀態,因為有某種無機物本身它會吸收東西,其實這種想像對科學家來講其實是一種非常大的快感,因為其實表示所有的無機物它都可能是某種生命,它可能自己沒有生命,它裡面不具有細胞,它裡面其實只有晶體的結構,可是它本身因為在這個環境裡面而讓它產生了生命的狀態。所以我會覺得這也是松志他在這一次他在選取的這些材料裡面,他用這樣的東西,在做一個有趣的探索,那要不要請松志談一下這次為什麼會選用這些素材。
陳松志:剛剛建宏老師提到大部分都在講我對於材料的處理,其實很多人會常常講把我的創作把它歸類在材質藝術範疇。我個人並不是完全認同在我的創作只看到材料的層面。對我來講,我在思考材質並不是把這些材質所謂經過全然地了解,然後應用它該有發揮的特性。其實我的創作脈絡裡頭我並沒有一個長久固定使用的素材,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素材去吸引著我讓我沿用很久。我覺得這裡頭有一個過程是,當你一但太熟悉或者是太充分的了解這個材質的特性的時候,材質就是材質,你可能會因應著這些材質它本來的屬性、它的狀態,它反而其實超越了你。那到最後可能其實就是變成一個技術性的操作,所以對我來講,有時候太充分的了解這個材質,它就會成為我離開那個材質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時刻。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每次在做這些,以材料來組合的空間創作的時候,它們特別的難的是,其實在於從發現實驗到執行的階段裡頭,這都不是歷經一個很長時間共處的狀態,往往可能這個時間最後被濃縮在一個執行層面的時刻,它很快地必須要被組合、組織,或者成為一個作品的形式。一但到這裡,最後當你已經開始了解它的時候,變成一個空間裝置形成出來之後,空間裝置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是,這個現場是會消失的,它就必須要結束!一切太熟悉或者是了解了其實就必須得學會「暫別」這件事情。所以對我來講空間裝置跟我在處理這些材料,某種共通性是,他們都不會永遠持續在那個狀態,它都是一個暫時性的,或者是說它一直持續地在改變,而且同樣的材料物料,它可能到不同空間,它們所面臨的狀態,條件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它並沒有一個就如同剛老師提到的所謂的一種化學的程式的這件事情,很多時候可能這個材料加這個材料在這裡一加一變成三,它可能到其他地方一加一卻變成了負。因為這其中會包含了現地空間的變因成分。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對我來講為什麼我在處理這些材料在不同空間裡頭,它都是一個非常困難,但也是引誘著我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然後當這些東西它被組合在這樣這些現場裡頭,其實因為人,包括我們創作者都一定會有很充分的感性,但又必須要在一個理性的空間、理性的節奏跟步驟方式中被建構出來。這個到最後其實我又希望能夠回到,它讓參與的人,所看到其實不應該是我,因為我對這個有所感那個其實是一個我個人的封閉系統,它不應該是成為我提供給你的知識也好,或者是指引。我認為其實每個人在這裡頭,都有跟這些空間存在一個交織的層面,我希望人在這裡頭透過他自己,其實你也不要管藝術家在想什麼,藝術家在想什麼這件事對你來講其實藝術家就是一個他者,那創作者在這裡頭他提供他的想像、他認為最好的事情跟你分享,你能夠吸收多少你就吸收,但如果你覺得吸收過多了,就像一個物質吸收了過多的成分,它到一個飽和度,它就必須釋放。所以回到當你看完這個展覽,某種程度上其實你什麼東西你都可以辨別得出來比如窗簾、地毯。到最後你都看的出來,鞋子、報紙,其實這個東西其實你也都可以辨識。但當你在跟別人描述的時候,誒那個展場有什麼?其實那是一個沒有辦法描述的事件,因為很多感覺的部分,很多心裡頭的層面其實是你會選擇性的你要跟別人表述什麼。我覺得那個放出來的狀態以及跟收縮回來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我希望在這些展場空間當中希望創造出來的「縫隙空間」。我期待讓介入的人他可以充分在這裡頭,保有他自己的一個私密性,這是後續在這幾年間我在處理的空間大部分著重思考的事情。
黃建宏:我在想剛剛松志講到一個,應該是這個展覽還蠻核心的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其實如果你們回去,人家問你們這個展場有什麼?然後松志他期待大家其實那個東西是講不出來的,那我覺得這是很多藝術家的企圖或是說很多藝術家的慾望。他會希望大家回去,人家問到這展覽的內容,那個東西是講不出來的,可是那個東西在,可是卻講不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很大的慾望展現,因為我在學校反而常常聽到的是「誒你們去看某個展覽,那個展覽裡面有什麼?」大部分都會這樣,「反正那個就是,譬如說一堆椅子,或這說一堆什麼或怎麼樣……」,也就是說我覺得剛剛松志的描述裡面,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面對你在這個創作裡面的另外一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其實是跟「詩」很有大的關係成分。因為我們如果稍微想一下最近其實非常流行比如說「思辨唯實論」或「物導向」等等這些跟所謂的物有關的一些新的想法。那可是在這些新的想法如果是依照這樣的想法來做創作或展覽的時候,它到最後其實通常呈現出來的東西給觀眾的想像它通常必須透過跟知識融合,也就是跟一些相關的客觀科學知識的融合,然後再去連接到可能對一些詩意想像的擴張。可是我覺得松志在這個展場裡面,我不曉得大家的感覺是不是都跟我一樣?我一剛開始進來的時候,會覺得這整個空間的第一個主題跟特徵是著落在那個地板上面,也就是它有一個地表,也就是說在松志他的一個操作裡面,其實他並沒有真的把它們變成是物,而是其實他很在意的去維持了一個地表的意象跟想像。所以一剛開始我看到這展場的時候,其實我會有一種錯覺,就是它是不是一張黑白照片?它會讓我有一種黑白照片的感覺。然後,如果在黑白照片的脈絡或想像裡面,當裡面又有一些鞋子,其實在歐洲這肯定就是跟戰爭會有關係的照片,或者跟一些離散有關的照片。可是當我們再拉回神來看,其實它似乎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其實它上面不是那種好像一些稀落的鞋子,而是密度還滿密集的擺著這些日常的運動鞋或皮鞋。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境底下,我稍微來想一下,因為剛剛松志也講到說,他其實不希望大家來看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是在理解陳松志這人是甚麼?或是希望這作品本身其實是有一個開放出去可以跟大家連結的層面。我在想在座有多少人念過或讀過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藝術作品的本源》,其實沒讀過也沒關係!我稍微先引用裡面的一個觀點,我不曉得如果有讀過的人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海德格在談梵谷的時候,為甚麼不大談梵谷?他在談梵谷的《農民鞋》,可是在那通篇文章裡面,梵谷很快就被帶過去了,然後全部都集中在討論《農民鞋》如何敞開一個大地,然後藝術家創造一個大地,這個大地跟世界之間有一個對抗的關係。你想想看他用的這些關鍵詞,藝術家好像變得不大重要,藝術家完成作品後就完成了,可是他的重要性在於我們如何去想樣藝術家創造大地究竟是什麼目的、意思?也就是說藝術家創造大地在海德格的那個年代中想像其實是有一個意象。那個意象是甚麼?我想大家有沒有那種經驗,比如說你開車或騎車,剛開始是一個緩坡上去,然後接著有一個急下的下坡之後,你如果上去了之後,你會突然看到一片海或者一片平原或是甚麼就敞開在你前面。那為甚麼會有那種效果?因為這其中存有著那個一個慢慢往上的一條地平線。因此為什麼地平線這件事情、這個詞在海德格的理論中是一個重要的詞,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人如何能有這個經驗。這個跟人在看日出、看日落的那一條線,所產生的那種感性的能力其實非常的有關的。也就是說人好像在越過一條線的時候整(這)個世界都將變了!如此般的理想就是說那個時候的人,他有這樣的想法有這樣的理想的時候,這件事情如何透過作品呈現出來?這其實是海德格對藝術作品的一個想像。可是這個想像他沒辦法用更理性地詞去說清楚,他只能夠透過這個經驗。那再回到松志的這個作品,我覺得到最後他說「無法專心的煙」,我好奇的是這邊有抽菸的有多少人?都不抽菸喔?所以都很乾淨!我們的世界都變得好乾淨,不過我們把抽菸的人當作不乾淨這樣也不對。我的話題是想帶到有沒有人看過王家衛的電影?王家衛電影裡面常常拍抽菸的人,然後你們有沒有人記得王家衛怎麼樣拍煙?有沒有人記得?如果不記得你們回去可以找《花樣年華》、《墮落天使》或《重慶森林》,其實你們都會找到王家衛拍煙這件事情。其實你們在這個展場始終沒看到煙,都沒有看到煙?可是有看!我就在想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為什麼大家看到煙通常會覺得浪漫?或者說看到煙,也就是煙這件事除了你覺得是火災之外,會比較緊張,要不然通常我們看到煙其實人會有一種情緒上面的波動跟轉移。那也就是為什麼抽菸的人也很喜歡看到他自己吐出來的煙,好像那個煙可以改變他的節奏。但大家都不抽菸,可能感受不到!回家可以燒燒看會不會有感覺。可是王家衛的片子你會看到當他在拍煙的時候,那個菸其實它會突然很怪。他在拍梁朝偉抽菸,先拍梁朝偉的特寫,然後會有一絲煙往上跑出框外,緊接下來他的鏡頭會往上移或往上切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當他在拍梁朝偉的時候是一種時間的節奏,當他往上拍煙的時候完全變了,也就是我們會想起影片中梁朝偉所發生的過去。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效果,當我們在煙裡面的時候,為甚麼你會突然從一個現實空間跑到另外一個空間?這件事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為甚麼那麼喜歡去看河或海?為什麼我要提示這些經驗,因為這些經驗都很奇特,因為這些東西它就存在在我們現實世界裡面,可是這些東西的律動它會突然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想法。我在想其實在松志的這個展場裡當然是更為複雜,可是我覺得這個詩意是存在的。也就是這些關於律動的問題,關於我們如何透過著律動跑到另外一個狀態?這些東西在松志的創作裡面是非常重要,所以他的作品比如說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他沒有要告訴你太多關於任何議題,比如說他不會去談空氣汙染的問題,他也不去談Cosplay的問題,或者任何的政治議題,其實他都沒有要去談這些事情。可是在他的這些材料裡面,比如說我們剛踩進來的時候,我們踩在這些活性碳或踩在地毯上面,我們把活性碳壓的更碎或怎樣等等這些感受,就是說當你踩在地毯上跟你踩在一般的展場的地板上面的那種感覺經驗幾乎都不一樣了。剛剛在跟《藝術新聞》雜誌主編鄭乃銘聊的時候,其實我們突然都對一件事情異常的著迷,這個東西可以待會再看松志可以怎麼樣去談「詩」這件事情。我們突然感覺到「油」這件事情在這其中也是很重要的!你想想看喔,我們通常會覺得油,其實是一個連我自己都很不敢面對的事情,也就是說油要我自己面對的時候,好比在點滷肉飯、控肉飯的時候,其實會很期待那個油量,那個食物油亮的感覺!可是其實如果沒有食物擺在前面的時候,想到油這件事情就會想到自己,那是很殘酷的事情。所以往往都不大敢想油的這件事情。也就是說油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它到底在什麼樣的時刻會產生不至於讓你太快產生噁心的感覺?油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在很多時刻,我們在描述噁心的時候或這描述一些不好的感覺時候,其實會常用到油這件事情,油這個意象或油這個字。只是其實油這件事情如果把他拉回到這個展場裡,去感受或者去觀看松志所處理出來的「油感」,我覺得那裡面有一種感覺在生活裡面,有一種有趣的「油」!你回想看當你在看著你穿了很久的一雙布鞋,而你又很久沒有再回去穿它,然後當你有一天你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到底那雙鞋子剩下多少痕跡,也就是說在鞋子表面上的那個油亮其實是可以看出這雙鞋子的壽命或是說可以看到這雙鞋子的歷史。這其實是一個有趣的事情,那麼究竟什麼時候你所看到的那個油會變得漂亮?好比如果你剛請你喜歡的一個人到你的面前來喝個下午茶,喝完他回去了對不對,然後你在收杯子的時候,你發現杯子上有他的一個嘴唇印,不一定是口紅印,因為男的喝也會有留下那個非常薄的一層油,或者他手拿著杯子的所留下那一層薄的油痕。我會覺得其實在看松志的作品的時候,那般很薄層的這個感覺其實會變成是一個他帶給你記憶中很重要的痕跡。為甚麼我會特別去講這個,好像非常小的細節,這個待會可以看松志怎麼談。再來談到有關我所看到的這個空間,其實面對這個空間本身看完的第一次感覺,我看待這是一個被撕裂的空間,被撕碎的,那撕裂不是心理上的撕裂,並不是說這個空間是在談松志的創傷或是怎麼樣。而是這個空間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像是碎掉的!然後這個碎裂它有一個機會讓這個空間將不再是一個具體或具有某種形式的空間樣態。也是因為眾多這些碎掉東西的組成,我會突然的感覺這個空間它同時好像很豐富!因為他有很多很細很碎的東西,但它同時,讓你不曉的焦點在哪裡?重點在哪裡?我覺得這是這次松志他在做這個空間裡頭給我的另外一個驚喜。這是我察覺他在空間處理的特質,因此我特別將它先提出來。除這點之外還有另外一點跟空間有關的提問,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越來越多年輕藝術家,其實都對於處理空間越來越感興趣。這方面可以當未來有機會可以再聊,可是我們就先回到有關處理空間的個部分看看松志有沒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陳松志:其實剛剛建宏老師有提到一個時間性的問題,還有提到所謂的地景這件事情,我想當我們踩踏在這個空間一進來時你會連結到地表或是地貌,其實我在做這個展覽的過程當中,讓我去思考到一件事情,某種表面上所看起來的「寧靜」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假象,就像人的思考其實是它隱藏在你的腦內,你也許看起來是一個很靜態的狀況,但事實上你的身體、你的意識其實是一直不斷的在動的。那這個其實讓我回想到就是說我聽過一個諺語:「人將不會踏在同一條河流之中」,因為那個河底的時間是一直不斷的在流動的。那當我們再探討到時間這個趣味點,其實時間是被人所定義出來,包括時區,有關時區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假的界線,也許透過人為的經緯度,來劃做所謂的時區,我認為區分這個界線如同是在找形(界線)的過程?那究竟找什麼是形這件事情?就變的相當有趣了。剛剛建宏老師提到一個所謂撕碎的這個世界,其實我覺得尋找的過程,就像我們如同在進行拼圖,或者是你把一張原本被撕碎掉的形之後,你怎麼去收拾這個殘局去找回它原本的形態。這個動機其實是源自於時間、空間之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會因應生活裡的事件、去回應處理這些現實狀態的總總,在這些產生的擾動影響裡,創作者他在進行塑型、找形的這動作。我常常運用到很多所謂不穩定性的材質,我覺得這個不穩定性我一方面想要凝固它,但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它們永遠有一個物理的原則,它在抵抗這個非物理的環境。我覺得在這個尋找的過程它反而是一個界於起始跟最後看到結果之間,我倒覺得那個過程反而是一個「經過本身」是最有趣的狀態。剛剛建宏老師有提到很多王家衛的電影,包括抽菸這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看到人家抽菸或是你自己抽菸的時候,你會發現為什麼人要抽菸?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你希望在這個持續的生活進行當中,它留住某一個短暫的片刻,你必須放下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來專注一件事情,我覺得那是一個假象靜止的時間,時間並沒有因此而停住。我們將重心建構在一根菸的消逝,另外一個煙的揮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我覺得這裡頭關乎作品中剛提到那些所謂流動性的這些、流變性的這些物質,它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要讓這些消逝跟介入的東西,它們同時並存在這個狀態,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相對的。那再回到建宏老師提到「油」的部分,我覺得人的身體需要有油,但也同時需要有水,可是油跟水本身其實是相斥的,但在我們的身體機能油和水其實是需要達成某一種平衡的關係,它才能共存,否則其實它就失衡。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放到我們思考到生命體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滿關鍵的一個成分在這裡頭。首先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有關於這個「變」的這件事情,其實我們身體不斷的在變,你每天吃的油脂、你喝的水,它就是一個不定型,我們永遠覺得我們的鞋子固定是穿幾號、身體是穿什麼尺碼,可是其實你的身體是不斷的在收縮跟放大的,那是一個很彈性的變化。我的創作其實是某種程度上是在顯現追求那個彈性的本身,而不是在尋找那個最放的、跟最收縮極致的狀態。
黃建宏:我在想把機會給來的現場朋友,有沒有人要提問的?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你們剛剛都有在「無法專心的煙」現場感覺嗎?
陳松志: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我想補充一個我的觀察,其實剛剛大約兩點鐘的時候作品現場陸陸續續有一些人,包括剛剛這些來參觀的朋友們,其實在現場我看到一個滿有趣的景象,我覺得那個現場很多人在其中大致看起來很像是「失魂」。原因在於在這個空間裡其實你也不知道你要看哪裡?然後你又沒辦法專心跟你的對象聊天!因為你其實知道腳下這個地毯表面充滿了不穩定性以及作品本身它滿脆弱的。或者是你也不希望那個粒子掉到你的鞋子裡頭或弄髒你自己的鞋,還有一直不斷的聲響,它不斷地擾亂你的身體的各種感覺。所以其實變成大家在裡頭走動的時候,其實非常的不自在,這件作品同時引出了你最多的感覺然後感覺盡出,最後我形容有點像是喪屍,或者是那種我們講失魂落魄的樣子。這是我觀察到的一個現場狀態覺得還滿有趣的。
黃建宏:有沒有人要講一下?我想你們現在不會只是觀眾,你們已經進到這個畫廊主人已經在這裡奮鬥十年,你們就坐在她們奮鬥的地方,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陳松志:我想這個今天這個活動,就是我們被濃縮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擠下這麼多具有油脂、水分的人,這個所謂生命體,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看到就在藝術其實給藝術家最大的空間,它願意把所有最大的空間提供給藝術家,然後我們今天大家集中在這麼一個角落裡頭,為了是能提供藝術家最完整的創作空間,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尺度了。
黃建宏:大家沒有想要講什麼嗎?如果沒有,你們要繼續聽我講事情嗎?我講事情會很像上課喔!真得要繼續講吼?我們來就是我剛剛其實有預設丟出一個問題,大概也是我對所有藝術家的展覽,剛剛其實有提到一件事情可以再補充一下,剛才有談到分子這件事情,也就是對於材料的選取,開始去選一些吸收性的、有所謂的專一性的那種材料,一些特殊、特性的材料,一直到松志對於「詩的意象」裡的堅持,也就是說從那種我們對分子世界想像那種流動性,一直到那種詩的意象的那種想像,其實它的層次跨越的非常大。如果這回到我作為一個觀者本身,我對藝術家的展覽其實都有一種期望,藝術家是一個個體,基本上作為一個個體,那他在進行表達的時候,這個時候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翻轉出一個我們開始對比較不是那麼只是自己問題的問題去進行思考或想像。這件事情會讓我想到一件事,因為昨天是北藝大這屆的畢業展,這屆畢業展發現有好多年輕人都做跟空間有關的創作,當然大部分跟空間有關的創作其實他們基本上最大的特質都專注在劇場式的空間,也就是讓空間具有某種敘事的感覺。他們都是大學部,當然有很多地方都還不夠成熟跟精準,可是我在想現在的人到底為什麼對空間有一種特別的期待,而不是非常專注的在做作品?其實有一個很殘酷的事情是什麼?也就是說在普遍學院裡都有的現象,有一些比較有進步精神的老師,有時候就會告訴學生說你為什麼要那麼作品化?也就是在學院裡的創作就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那麼作品化的呈現嗎?你為何要把你自己那麼封閉在一個物件上面嗎?或者一幅畫面上?通常這樣的事情對於年輕的藝術家來講,就是還在學習的學生藝術家來講,他馬上會產生一種迷惘,其實松志也是老師,也可以參與在這裡面談。這個迷惘就是要如何做出不像作品的作品?我不做出那個物件,那我要做什麼?通常同學其實如果先擺脫做物件或做物品這件事情,是一個制式化或體制所想像的事情的話,那在創作中越出這件事情我到底可以幹嘛?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人都會先往空間走,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空間究竟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希望?為什麼我們從體制的一個規範,就是我們就是要做作品的這件事情脫離的時候,大家會先去想空間?我會覺得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人,如同我一剛開始講的,即使這個地方現在是你沒有去過的,那個地方對你來講可能都是已知的,因為我們今天有太多的訊息告訴你什麼空間就是什麼用途?什麼空間你可以做什麼事?甚至連白盒子之外到底我們可以幹嘛都經非常清楚,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空間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或者相對相反過來,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年輕學生藝術家他們對空間有一種非常大的嚮往,我會覺得其實這跟姚瑞中他們年輕的時候,當他還是北藝大學生的時候,然後他們去佔領一個地方然後叫做「非常廟」那動機是非常不一樣的,那個非常不一樣的狀態是說,當時他們這些年輕人佔領一個空間,那些空間是沒有人管的!可是其實今天為什麼年輕人對空間有一種很像一種渴望,可是又表示這可望非常難實現,我想就是現在即使是廢棄的地方,看起來像是廢墟的地方都有產權,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對於空間的想像其實會因為所有的空間在城市裡面都越來越被產權化,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空地沒有人要,然後隨便你去做任何事,這種機會已經非常非常少!更何況來念藝術做當代藝術,大部分都在城市裡面,其實這件事情就更難被發生。因此我會覺得就是在這個狀況底下,如何帶出如何有能力把一個空間做出我要的感覺!把一個空間做成什麼感覺?這裡面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慾望,所以我覺的應該是在一個空間取得一個越難的地方,或越嚴苛的地方,其實藝術家會越被逼往這個方向去思考。也就是說我如何創造出因為這很像煙霧一樣,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到一個地方展覽,其實除非你跟這個屋主或這個所有權的人有建構某種常態的關係,你才有可能永遠留存在這個空間,要不然其實這些空間都很像煙霧一樣,藝術家在面對一個檔期,到底可以留下什麼?除了交易紀錄之外,就是說你待會在一個空間可以留下什麼?這其實會變成一個藝術家需要挑戰的事情!雖然大部分的藝術家還是選擇用作品,因為其實這個最簡單,就很像當你像想不出你要買什麼東西給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時候,通常就是買一個小東西,因為小東西最簡單。所以其實到底怎麼樣去讓一個空間有不同的感覺,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會成為今天年輕人的一個慾望,我不曉得松志你也當老師也是一位藝術家你怎麼來思考?
陳松志:其實常有人會問我到底我的創作是什麼類型?什麼屬性?我其實比較會去強調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是在處裡複合媒體在空間現場裡頭的現地呈現。基本上我們會簡稱為現地裝置或空間裝置。其實我要選用什麼材料它都是多重選擇,所以基本上去取決於先有空間才知道要放什麼素材進去,所以這些空間本身它的架構它的基礎可能都跑在我的原先我的發現、我的收集以及設想之前。也許你收集了原本生活裡頭你的感性它根本放不進那個空間,因為這些空間本身它太強大了,因為我覺得任何空間,白盒子有白盒子空間的強大,黑盒子或者是一個廢墟在透過藝術行為介入它都需要面臨不同挑戰的層面。剛剛建宏老師其實提到的一點人嚮往廢墟,因為在那個廢墟當中,你往往可以看到從廢墟裡頭長出來的一株小草,或者是你還存在在這裡,它還有某一種生命在這個看似快要無機的狀況下,它產生出來的一個力道。反過來講,我覺得其實在一個廢墟空間來創作,我認為那是很容易借力使力,因為廢墟本身就很豐富!它本身就很多歷史的痕跡層次在那裡頭。我反倒覺得對我來講在白盒子做空間它相對是難的,因為白盒子很明顯就是垂直水平的線軸不斷地轉折在這裡頭,那如何把那條線拿掉?我如何在這裡頭製造出一個可能往廢墟走的意象?也許它是一種心理層次的廢墟,因為我不可能製造出一個真的廢墟,或是趨近於真正廢墟的一個空間,所以為什麼我在處裡「就在」這麼多次經驗裡頭,我覺得越對它越瞭解才知道它的難處,那因為這個難處其實我希望用另外一個方式去面對它!你也可以在這次展覽裡頭看到幾個黑色的布幔,這個畫廊看起來很完整,天花板挑高也夠高,可是它還是有一個它原本畫廊空間裡頭的痕跡跟造型,再加上它必需要符合某種機能性,比如說這裡要有辦公室、這裡要有通道,老實講對我來講如果我要一個純白的空間就只要讓大家看見作品,其實這些辦公室的開口、廊道所產生出來的洞孔跟光線,對我來講就是干擾!我如何把這個干擾涵蓋進去?像茶水間它需要有一個排風口,因為要有冷氣傳送,那我索性把排風口變成一個聲道,讓它感覺從茶水間裡你有股另一個很日常生活裡頭播放著的持續音樂,它是一個很生活的情狀串流。然後在很多縫隙的空間裡頭我夾了一些廣播的現場,那些內容其實不是我主導,它是一個調頻,它其實一直持續在進行的,它是一直在變的現場空間延伸,那有什麼是不變?你看到的那幾個黑色的布幔它其實根據這個空間入口尺寸一比一,量尺的尺規,變成一個遮蔽的通道,它暗示著這裡好像有另外一個空間,它變成另外一個造型,它形成了一個對照的關係。因此你說這幾個黑色尺寸它離開這個空間它可能就失去意義,因為它是之於這個空間它們有一個相對的一個角色對位關係在這裡頭。我總歸來講,這裡頭有太多太多的線索,如果我們用詩詞的方式來建構或表達這件事情,如何讀懂一首詩其實是滿深的學問。雖然詩的結構並不長,但詩基本上在很有限的文字裡頭,必須創造出最多意境,創造出最多豐富層次的語境,或者是語意。那裡頭其實有各方的詮釋,懂不懂不重要,如何想要讀懂?或是在讀的過程,就是一個滿重要的體驗。所以對於這個「無法專心的煙」它其實涵蓋了的就是這麼一段找尋的過程。
黃建宏:那個時間就是快差不多,我在想大家有沒有一定要追問的問題或者說要問的問題,可以趁這個機會來問藝術家,我在想就是說台灣的藝術家應該有快二十年年輕藝術家其實都在思考到底要怎麼抓住稍縱即逝,或者說瞬間,也就是說不會留太久的東西。那種感覺到底要怎樣被掌握住?然後雖然它在非常短的瞬間發生的事情,它在這麼小的瞬間又一直在變,其實有非常多藝術家都在想這件事,可是我們會發現雖然大家在唸書的時候有很多藝術家在想這件事,可是你會發現當很多藝術家開始進入藝術圈開始進行專業的創作的時候,越來越少藝術家還那麼專注來面對這個問題,因為這個東西它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大部分藝術家還是會選擇建立風格,所以這裡面並不是在講風格是好或不好,而是要讓人家知道說你這風格是像設計一個Logo那麼快就成立了。還是你這風格其實讓大家講不清楚那裡面到底有什麼,這其實也可以變成另一種風格的發展。松志的創作風格究竟是哪一個?我想這就留給大家可以再去想一下,可以再跟松志繼續交流的一個問題,我想大家都比較想要跟他私聊,私聊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事情,那我們今天就先謝謝就在藝術給我們這個難得的機會,然後再謝謝松志。謝謝大家今天過來。
引言人:林珮鈺(就在藝術空間總監)
與談人:黃建宏(策展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所長)
陳松志(藝術家)
林珮鈺:哈囉大家好!謝謝你們抽空過來參加這次展覽座談會,我是就在藝術空間的總監林珮鈺,這次展覽其實是安排在就在藝術十週年計畫裡面的第二個部分。這次就在藝術十週年計畫特別邀請黃建宏老師來策劃。在二月份,已舉辦過第一檔的是土耳其藝術家哈廷.奧倫利(Fahrettin Örenli)的個展,這一次進行到第二個部分。這一次就是由我們自己的代理藝術家陳松志,這已經是這位藝術家與就在第五回的合作個展,這次展覽又會和這個空間產生什麼火花,我們今天就直接進入主題,特別邀請策展人和藝術家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黃建宏:我在想讓藝術家充分的表達他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先稍微來做一下襯底的工作,也就是說到底可以在什麼樣的故事背景底下來了解?或者說來感受松志的作品,我在想就是剛剛珮鈺已經有說到起因於十週年的一個策畫。在第一檔展覽,我跟珮鈺談及,我要找一個藝術家是在台灣大家都不熟悉,然後她自己也不認識,就是要找這樣一個藝術家來證明這個畫廊的實力,因此就找了一位土耳其藝術家哈廷.奧倫利。然後在第二檔展覽就是目前的陳松志,以及第三檔展覽的周育正。當初有這樣一個思考在於這三檔展覽其實有三種藝術家,一個藝術家是珮鈺完全陌生的,那就是試她的膽量。然後會有一檔展覽就是她長期合作的藝術家,也就是她持續經紀的藝術家展現的是就在的累積以及藝術家的突破。然後再有一檔展覽是她有合作過但是沒有經紀的藝術家,這點要試試「就在」的開放程度。我們會知道對於一個空間的經營者來說,其實面對這三種藝術家其實那個心情跟狀態其實都會是不一樣的,甚至在處理空間以及作品上其實都不一樣。那這三檔之中又特別是松志這一檔,最初是要請他要做一個空間,這空間是要做什麼?其實珮鈺在六月初的時候,她會邀請其在亞洲同樣是當代藝術空間的經營者一起來跟她對話,也就是他們要去交流到底像這樣一個中型藝術機構,或者甚至中小型的畫廊在今天的亞洲是有可能可如何運作?所以松志他原本,他其實最初我們在跟他協商或者說在跟討論合作的時候,就是希望他做出一個開放空間,這個空間是我們要在這裡面要去激發一些想像。那周育正的部分其實他就是可以進來這個空間,然後如何營造一個機會是可以跟其他藝術家合作,所以這個我就先不爆梗,後續你們接續到第三檔展覽的時候就可以過來看一下藝術家會怎麼來處理。那回到今天的主題,在這裡我覺得稍微再講一下這個空間,你們可以感覺到這裡其實就是一個辦公室,辦公室感覺上是一個非常功能性的地方,可是這辦公室其實是珮鈺她一剛開始,也就是當時有四個人要一起去做跟藝術有關的理想,然後在想一些新的路子,一剛開始在網路上面去做,最後進行到這個實體空間,以及她們開始意識到似乎要做一個實體空間來經營的這件事情,這四個人在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大的桌子曾經是一起工作著的。到最後卻只剩珮鈺一個人在這裡持續下來?我想這裡面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座談今天就乾脆進到她的辦公室來談,這是有意思的!因為我在想所有的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者說你在開始個人生涯的時候總會有一個地方可能是對你來講是重要的,然後它同時也陪伴著在這裏面發生所有的事情,因此我覺得大家今天的對話或許就應該在這裡,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還有一個「轉折」就可以開始今天的對話。這個「轉折」話說這在一剛開始也是未知的!因為假設有一個狀況,你原本找一個建築師或者室內設計師跟他說:「誒你幫我們來設計一個空間或幫我們來創造一個空間」。然後我們就找到松志,然後當這個人做完空間他把空間裝設好了之後,他就告訴你,你將不能在這裡做任何事情,必須要尊循我的創作。大概在松志之前,我只知道一個人這麼幹的就是安藤忠雄!他蓋好了美術館然後去確立的這個廳要放什麼作品,他簽了約說五年不能動,甚至椅子都是他選的,也表示五年不能動。還好松志沒有像安藤忠雄那麼殘酷!也就是那個空間狀態在完成後的五年都將不能改變。所以我在想其實像這樣的合作,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既然今天松志面對的是一個空間,那我覺得因為我們就是在藝術裡面在談論這件事情或來思考這件事情或感受這件事情的話,我覺得有一個最基本及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最難的事情,就是怎麼樣讓空間變成是未知的。其實這件事情非常難,因為其實大家現在都很厲害,我相信處在這空間裡面,很多人其實都很敏銳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每個人進到一個空間到底要做什麼事或要幹嘛其實都非常清楚!其實今天很少人還會進到一個空間然後他會感覺到害怕,或者他可能覺得陌生。你會發現我們可以來進行一個旅遊的規劃,也就是說我怎麼樣在這個旅程中面對的全部都將是我陌生的空間環境,譬如我今天要去京都玩然後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地方,但其實你會發現今天的你,即使你以前從來沒有去過,可是京都的空間其實已都是你可以想像的。甚至這些城市環境他們幫你規劃的很好,也就是說當你到一個新的城市其實所有的空間其實都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從來沒有來過。所以我在想松志或許帶給我們一個最寶貴的經驗,應該是他如何讓這個空間是未知的!那個未知並不是你沒去過或者是你沒看過他的照片或者是怎麼樣,而是到底那個感覺怎麼樣被創造出來!所以接下來我先丟出這個東西然後待會我可以再多說一點,我們就先讓松志說一下。
陳松志:謝謝建宏老師,謝謝大家今天下午來這個地方參與我們的座談,關於剛建宏老師提到的部分,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早就理解到這應該會是一個要能提供「人」與「事」可能可以參與其中,可能可以在裡頭有很多事件的空間調性。對我來講我覺得那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恐懼的本身,就像我的英文展覽名稱A Fork in the Road,它其實都是一個選擇,你選擇了這條路,必然要放棄另一條路,因為你只能走在一條路上。或者你可能要倒頭回來再去走另外一條路。因此我在思考這個展覽的時候,其實在面對的是一個我很熟悉的空間,也因為過度熟悉了,其實你知道這空間裡頭有非常多的細節你不能迴避它!那對我來講,既然這麼的熟悉,但是它突然、頓時之間讓我少了某一種發現的趣味在這裏頭。於是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該怎麼樣去燃起在這個空間當中的最陌生的感覺,所以我就開始回應到那個陌生,其實我覺得陌生只有一種狀況就是當你在看不清楚的狀況,你就會對這個空間產生陌生感,因此對我來講或許這一次的展覽在展覽的作品呈現以及思考,我其實選擇了的是一個滿封閉的系統,所謂封閉系統就是我希望讓這個結構系統它是被遮蔽起來,包括這個空間它可能被地毯覆蓋了、被一些織品等總總的東西覆蓋了。因為覆蓋了這些東西讓你看不到了,你產生了更多的未知,或者更多的對於這個空間的延伸。事實上「就在」的空間並不大,但它卻有很多很零碎的格局,因為這個空間它本來就不是作為一個展場來使用,它原本建築就是一般的住宅的類型,那對我來講我如何在這個有所局限的範圍裏頭,讓這些阻礙讓觀眾因看不清楚而產生延伸。所以那回到一點就是,究竟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最後選擇一條路是回到一個最沒有聲音的地方。所謂沒有聲音,雖然你聽到這裡面有很多干擾的聲響,可是你可以選擇去聽或不去聽,或者你根本就聽不到!所以我覺得這個封閉的系統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我這一次的選擇,它可能不見得是我們講二元看待正面或是負面的,它就只是個選擇!所以嚴格來講,我其實覺得這個對於跟我合作的人反而其實是最辛苦的,也就是多數的時候我在做是事情的本身其實是容易的,但是在抉擇或者是在排拒誘導的過程是最困難的。因此這次最後你看到這個展覽表現出來的樣態其實很零散的,它其實沒有要說一件很明確的事情,也就像你從中英文字義上,中文字義的煙,它可能聯想到就是菸草,但它也可能是煙灰總總的……,它其實有太多開放的可能,作品本身其實即在探討那個抉擇跟擾亂的狀態。其實我覺得把這些人、事件移放到這個空間裡頭,在這裏發生的事物對這個作品本身其實也是個擾亂,那就是整個狀況有點反客為主,或者是這裏頭其實有一個迫使我們必須去做某種選擇跟決定這件事情。但我相信這個過程都是好的,也就是說我們人得要先面對問題,才有辦法穿越問題的本身,不然其實你就是被擋在這個表層之外,我大概先補充到這裡。
黃建宏:好。我再接下來講一些事,也就是先預告一件事情,就是你們會發現其實這個展覽到目前並沒有策展論述,因為其實策展論述都還在過程的進行之中,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合作的策展人然後我期待藝術家其實在給我一個我想像不到的空間,因為我覺得今天策展人的角色究竟是什麼?如果策展人的角色就是一個全知者好了,也就是說他已經很清楚這個藝術家是要幹嘛,然後他已經預知這個藝術家的作品,其實這樣的一個策展人除了做生意他還有什麼好做的。或是說除了做典禮之外還有做生意之外,其實也就沒有什麼好做的。因此我還是會期待松志他到底可以帶給我或我們什麼樣的表述空間?既然這樣的話,其實策展論述就不可能在作品展覽還沒發生完成這之前就寫完,所以既然松志他要處理空間,然後其實對於整個展覽來講的話,展覽裡面到底存在多少種空間其實論述本身他也是一個影響空間的事情,所以我其實會採取一種方式,假設他是一個料理空間的廚師好了,然後我將會定期來這邊感受這個空間,之後我會發表一些對空間的想法,我會錄音下來然後把這個當作食材交給他,然後因為這些東西這些材料他其實都是策展人自己講的嘛,然後可以是讓藝術家他試著從這些材料裡面去完成出一篇論述,就是說他不能自己寫自己的話,他要寫我的話可是是由他來寫,所以我也很期待到時候會不會寫出來一篇論述是我看不懂的,是我不認識的,我也在期待這樣的事情,因此在這個展覽的規劃裡面,其實會在很多的層次我都希望藉著松志的敏感度,了解藝術家對我們來講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們如果說比較功利一點的講,藝術家到底對我們有什麼用處,當然我如果有錢可以收藏跟進行買賣的話,那當然藝術家就可以提供我作品就會有某種投資的用處。可是我並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才要靠講話維生,也就是說我自己其實會這樣覺得,藝術家對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可以提供給我們感受不到的感覺,這個就是我覺得藝術家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提供這些感性的層次,甚至我如果跳得快一點,對我來講感性的層次越多,我們的這個世界或者我們的整個社會民主化程度的可能性就會越高。因為感受多才會讓人有想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連結,我不認為感受非常貧乏的人,他的思想會有趣,然後他的思想會真的有創意。所以這個也是我在這樣的一個機會裡面,我一直在期待松志這邊他能夠跟我產生什麼樣的交流跟互動,那我在這邊在帶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我覺得因為大家也都有看過那個空間,或者說去感受那個空間,我在想大家在感受過以後然後就走過來裏邊,然後我們開始來談這件事情其實是還滿有趣的。我覺得我先講松志的,就是說我自己整理出來松志的某種操作作品的思考方式,我個人覺得日常的感覺對松志來講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一個人在他的日常裡面到底感受到什麼?他到底覺得他處在什麼樣的情境底下、處境底下其實非常關鍵。然後松志他會把這樣一個日常處境裡的東西,不是直接把它再現出來,有很多的藝術家在他在感受到一些日常片段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藝術家處理的就是去放大那個瞬間,放大瞬間大部分都用錄像,要不然就是去放大那質地、質感,那可能會透過攝影或透過一些物件的呈現或堆積。這些藝術家其實他們在面對日常生活或日常性的時候,絕大部份都是在思考怎麼樣用放大的方式再現它。可是在松志的創作之中,其實我從來沒有跟他講過這樣的事,也就是說他是把日常所感受到的事情,他會去找到一些材料,並去設計一個工作的過程,我覺得他好像一直有一個偏執,這個偏執就是他一直要把日常的那個根本就非常難以具體化的東西,他要透過一個操作的過程讓它附著或黏著在那個材料上面。然後再把那個材料放回空間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他會讓你夾雜在好像一個「裂縫」之間的感覺,也就是說一方面你可以知道有日常的東西,可是另外一方面你會覺得他好像有一種非常偏執純化的過程。也就是說這兩種東西其實我覺得是在看松志大部分的創作裡面會讓人家感受到的展現,我會覺得這個感受是一個有意思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裡面,除非你對於你生活的控制能力可以到非常的高,要不然的話,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活在這樣的一個混雜性裡面,可是在這個混雜性裡面對於松志來講他並不是倚賴一個非常直接的呈現,而是它有一個操作過程,我會覺得所以我們在看松志的作品的時候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層次,我覺得大部分的層次或許都可以比較清楚,但我覺得他對待材料操作的那個偏執所帶有的情感,其實是跟藝術家本身應該是最為非常靠近的事情。我都一直沒有談到這個展場,於是我就大概先丟出我對松志他在進行創作的時候的操作思考,然後我們來聽聽看松志怎麼講。
陳松志:好!其實建宏老師有提到這次滿特別的像是回到一個作展覽跟做創作的過程,一直以來其實我們常談到創作中的獨立性也就是創作行為中的獨立思考。創作本身其實就要能夠充分發揮的的獨立、獨特精神,也就是過程之中要能思考到任何的創作都會跟他者產生關係,但對我來講有時候跟人在互動上那溝通的本身,對我來講就是一種是一個還蠻難進行的一個抉擇以及過程。因為有時候當下決定了這件事情其實我後來很快的就反悔了,這其實包含了一個允諾的過程,所以對我來講我歷年的創作裡,當初十週年計畫的三個部分裡頭,建宏老師跟珮鈺這邊也思考到,好像要把我跟其他的藝術家搭配在一起做一個組合確實是一個滿困難的事情。因為好像那個東西是你把他(它)放在那個位置裡頭但他(它)好像又變成了不屬於自己了,他(它)可能會被依附在另外一個或是消失在另外一個他者的內裏裡頭了,所以我覺得這裡頭回到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一個個人秀了。所以我覺得建宏老師在這裡也提供給我一個非常充分的空間,以致後來我在思考到這一次的整個展覽的節奏裡頭,建宏老師丟出了一個後論述這件事情,因為其實老實講,我要做什麼其實似乎連我自己,都有可能在製做的這個當下可能還在(會)改變。其實沒有太多人能夠知道到底我要做什麼,所以那這裡回到一點就是信任的問題,回到是一個人根本裡頭,你對於這件事情的信任。我真的覺得我非常的幸運我有一個很信任我的畫廊主,有很信任我的策展人,這是一個蠻複雜卻難得的經歷,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也讓我在這裡頭很充分的讓我有多一點的時間來讓這東西就像一個濾化、沈澱的過程一樣。所以當我先有作品,做完之後我們這次的策展我們一開始在對外的訊息裡頭,其實我們丟出的不是策展人的論述,而是藝術家的自述,這個回到以前的個展當然也就是這樣,但這次一樣的,讓我以我自己的自述,那其實是對我來講,先有作品完成之後,這份自述文字是另一種再創作,因為我必須要用文字的系統、語言的系統、表述的系統來釐清我自己的琳琳總總。這是一個從開始進行到凝視個人創作的部分。以致到後續這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觀眾在這裡頭總總的參與,讓我們彼此有更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也在後續才會產生建宏老師在作品裡頭持續的、多一點的展覽細節內容分享。我剛想到這個東西好像是很有趣有點,像是你們在展場裡頭看到最大面積的活性碳原粒,活性碳粒它原本的素材其實來自於植物的有機狀體,那好比就像我創作出來的東西,慢慢地經由一個策展的系統,他者論述的系統慢慢地經過一個濾化的手續最後被呈現出來。我覺得那一個最清晰的處理,它讓彼此都充分表達,然後就形成的總體成為我們樂見看到的。它保留了策展人的言說,同時也讓藝術創作者在這裡頭能夠選擇創作中封閉的部分或有願意開放出來的部分可以進行適時、適應的表達。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蠻特殊的一個展覽製作與跟策展進行。
黃建宏: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展場裡面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對這些事情的想像,以及對松志創作的一個想像。對我來講因為我自己以前是學化學的,所以其實學化學相較於其他的學科,或許會多有一種奇特的想像力,來自於對於所謂分子的世界,總會有一些特別的幻象。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必須背很多的分子式,然後我們還要背元素表,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本來就有非常多的粒子,因此大家也都會說現在世界是原子化的世界,然後有非常多分子。包含我們以前在買藥的時候會去表述出上面的成分,基本上在廣告的時候更會表達出內容的成分細節,這大部分都還是一個非常類比世界的思考表達。比方說這個藥品是來自什麼植物或是來自於什麼,也就是說那都還是存有一個外在型態的表達。可是你會發現現在大家在談論營養食品或者藥品的時候,其實大家可以對這些分子式的學名都朗朗上口,其實我們的世界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其實在發現影響我們的東西越來越是在那些看不見的分子,也就是大家被說服了!而且大家現在開始跟學化學的人一樣有一種幻想的能力了。也就是說你為什麼會覺得你去吃一種叫做某某化學式的東西,然後你就覺得你的身體改善了,其實這是需要靠非常巨大的想像力。這次松志其實他選了一個很有趣的材料,因為如果我們就這次展覽裡面,松志選了不同層次的素材,然後我會覺得這些材料都是非常的有趣。很多的藝術家在選材料的時候,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大部分的藝術家在選素材,當然我們很多都是處理視覺的,所以在一剛開始選擇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會根據它的質地、它的紋理、它的型態都會有關,因為這個跟我們的視覺其實是非常直接聯繫的。接下來我們因為在教科書上學了、看到了杜象(Marcel Duchamp),當然我們很少看到杜象的原作,大概都是看到他作品的圖片,於是我們就會開始去想像工業製品它在一個文化上面跟我們人產生了關係,所以開始有這一個層次我們為什麼會選這個材料?其實會有存在這樣邏輯層次思考的關聯。然後接下來當這個世界很多都在討論檔案的時候,甚至在討論所謂的證物美學,就開始將所有的物都依附在一個歷史的脈絡底下,開始去尋找這個來歷。從十年前開始可能就會有一些搞植物的藝術家,譬如說特別是香菇的培育或是說黴菌的培育,大概在十年前在巴黎東京宮就曾做過這樣的展覽。也就是開始當我們在對空氣裡面的味道,我們開始是用粒子去想像他,這感覺上好像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些想法,可是到底人如何把這個想像真的具體的呈現與相信,其實這需要很長的時間。我覺得這一次很有趣的是松志他選擇了活性碳,如果你從今天的日常生活裡面你會發現,現在有越來越多人他會告訴我們各式各樣的知識,怎麼樣的東西它會產生什麼作用,這些作用其實可能會對人造成有害或對人產生幫助。所以我們如果說藝術家他並不只是帶給我們視覺上的東西,而是他必須要開放或者必須要在創作上能擴張我們的感性。那很能看出松志這次他選用了活性碳其實他裡面有一個滿有意思的角度,並不是說松志讓我們看到的粒子,我想松志沒有這種魔力,他可以讓我們看到空氣裡面的分子,可是他開始試著在選取一種材料,也就是說你會看到大部分他所選取的材料不管是活性碳、地毯、或是他是自己穿過很久的布鞋或皮鞋,還有那些被油墨重新刷過的報紙,最後塞進去鞋子裡面。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事情,這些材料的共通性是什麼?它們都有吸收性,所以其實我們到底要如何讓這種吸收的狀態,因為有某種無機物本身它會吸收東西,其實這種想像對科學家來講其實是一種非常大的快感,因為其實表示所有的無機物它都可能是某種生命,它可能自己沒有生命,它裡面不具有細胞,它裡面其實只有晶體的結構,可是它本身因為在這個環境裡面而讓它產生了生命的狀態。所以我會覺得這也是松志他在這一次他在選取的這些材料裡面,他用這樣的東西,在做一個有趣的探索,那要不要請松志談一下這次為什麼會選用這些素材。
陳松志:剛剛建宏老師提到大部分都在講我對於材料的處理,其實很多人會常常講把我的創作把它歸類在材質藝術範疇。我個人並不是完全認同在我的創作只看到材料的層面。對我來講,我在思考材質並不是把這些材質所謂經過全然地了解,然後應用它該有發揮的特性。其實我的創作脈絡裡頭我並沒有一個長久固定使用的素材,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素材去吸引著我讓我沿用很久。我覺得這裡頭有一個過程是,當你一但太熟悉或者是太充分的了解這個材質的特性的時候,材質就是材質,你可能會因應著這些材質它本來的屬性、它的狀態,它反而其實超越了你。那到最後可能其實就是變成一個技術性的操作,所以對我來講,有時候太充分的了解這個材質,它就會成為我離開那個材質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時刻。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每次在做這些,以材料來組合的空間創作的時候,它們特別的難的是,其實在於從發現實驗到執行的階段裡頭,這都不是歷經一個很長時間共處的狀態,往往可能這個時間最後被濃縮在一個執行層面的時刻,它很快地必須要被組合、組織,或者成為一個作品的形式。一但到這裡,最後當你已經開始了解它的時候,變成一個空間裝置形成出來之後,空間裝置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是,這個現場是會消失的,它就必須要結束!一切太熟悉或者是了解了其實就必須得學會「暫別」這件事情。所以對我來講空間裝置跟我在處理這些材料,某種共通性是,他們都不會永遠持續在那個狀態,它都是一個暫時性的,或者是說它一直持續地在改變,而且同樣的材料物料,它可能到不同空間,它們所面臨的狀態,條件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它並沒有一個就如同剛老師提到的所謂的一種化學的程式的這件事情,很多時候可能這個材料加這個材料在這裡一加一變成三,它可能到其他地方一加一卻變成了負。因為這其中會包含了現地空間的變因成分。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對我來講為什麼我在處理這些材料在不同空間裡頭,它都是一個非常困難,但也是引誘著我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然後當這些東西它被組合在這樣這些現場裡頭,其實因為人,包括我們創作者都一定會有很充分的感性,但又必須要在一個理性的空間、理性的節奏跟步驟方式中被建構出來。這個到最後其實我又希望能夠回到,它讓參與的人,所看到其實不應該是我,因為我對這個有所感那個其實是一個我個人的封閉系統,它不應該是成為我提供給你的知識也好,或者是指引。我認為其實每個人在這裡頭,都有跟這些空間存在一個交織的層面,我希望人在這裡頭透過他自己,其實你也不要管藝術家在想什麼,藝術家在想什麼這件事對你來講其實藝術家就是一個他者,那創作者在這裡頭他提供他的想像、他認為最好的事情跟你分享,你能夠吸收多少你就吸收,但如果你覺得吸收過多了,就像一個物質吸收了過多的成分,它到一個飽和度,它就必須釋放。所以回到當你看完這個展覽,某種程度上其實你什麼東西你都可以辨別得出來比如窗簾、地毯。到最後你都看的出來,鞋子、報紙,其實這個東西其實你也都可以辨識。但當你在跟別人描述的時候,誒那個展場有什麼?其實那是一個沒有辦法描述的事件,因為很多感覺的部分,很多心裡頭的層面其實是你會選擇性的你要跟別人表述什麼。我覺得那個放出來的狀態以及跟收縮回來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我希望在這些展場空間當中希望創造出來的「縫隙空間」。我期待讓介入的人他可以充分在這裡頭,保有他自己的一個私密性,這是後續在這幾年間我在處理的空間大部分著重思考的事情。
黃建宏:我在想剛剛松志講到一個,應該是這個展覽還蠻核心的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其實如果你們回去,人家問你們這個展場有什麼?然後松志他期待大家其實那個東西是講不出來的,那我覺得這是很多藝術家的企圖或是說很多藝術家的慾望。他會希望大家回去,人家問到這展覽的內容,那個東西是講不出來的,可是那個東西在,可是卻講不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很大的慾望展現,因為我在學校反而常常聽到的是「誒你們去看某個展覽,那個展覽裡面有什麼?」大部分都會這樣,「反正那個就是,譬如說一堆椅子,或這說一堆什麼或怎麼樣……」,也就是說我覺得剛剛松志的描述裡面,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面對你在這個創作裡面的另外一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其實是跟「詩」很有大的關係成分。因為我們如果稍微想一下最近其實非常流行比如說「思辨唯實論」或「物導向」等等這些跟所謂的物有關的一些新的想法。那可是在這些新的想法如果是依照這樣的想法來做創作或展覽的時候,它到最後其實通常呈現出來的東西給觀眾的想像它通常必須透過跟知識融合,也就是跟一些相關的客觀科學知識的融合,然後再去連接到可能對一些詩意想像的擴張。可是我覺得松志在這個展場裡面,我不曉得大家的感覺是不是都跟我一樣?我一剛開始進來的時候,會覺得這整個空間的第一個主題跟特徵是著落在那個地板上面,也就是它有一個地表,也就是說在松志他的一個操作裡面,其實他並沒有真的把它們變成是物,而是其實他很在意的去維持了一個地表的意象跟想像。所以一剛開始我看到這展場的時候,其實我會有一種錯覺,就是它是不是一張黑白照片?它會讓我有一種黑白照片的感覺。然後,如果在黑白照片的脈絡或想像裡面,當裡面又有一些鞋子,其實在歐洲這肯定就是跟戰爭會有關係的照片,或者跟一些離散有關的照片。可是當我們再拉回神來看,其實它似乎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其實它上面不是那種好像一些稀落的鞋子,而是密度還滿密集的擺著這些日常的運動鞋或皮鞋。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境底下,我稍微來想一下,因為剛剛松志也講到說,他其實不希望大家來看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是在理解陳松志這人是甚麼?或是希望這作品本身其實是有一個開放出去可以跟大家連結的層面。我在想在座有多少人念過或讀過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藝術作品的本源》,其實沒讀過也沒關係!我稍微先引用裡面的一個觀點,我不曉得如果有讀過的人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海德格在談梵谷的時候,為甚麼不大談梵谷?他在談梵谷的《農民鞋》,可是在那通篇文章裡面,梵谷很快就被帶過去了,然後全部都集中在討論《農民鞋》如何敞開一個大地,然後藝術家創造一個大地,這個大地跟世界之間有一個對抗的關係。你想想看他用的這些關鍵詞,藝術家好像變得不大重要,藝術家完成作品後就完成了,可是他的重要性在於我們如何去想樣藝術家創造大地究竟是什麼目的、意思?也就是說藝術家創造大地在海德格的那個年代中想像其實是有一個意象。那個意象是甚麼?我想大家有沒有那種經驗,比如說你開車或騎車,剛開始是一個緩坡上去,然後接著有一個急下的下坡之後,你如果上去了之後,你會突然看到一片海或者一片平原或是甚麼就敞開在你前面。那為甚麼會有那種效果?因為這其中存有著那個一個慢慢往上的一條地平線。因此為什麼地平線這件事情、這個詞在海德格的理論中是一個重要的詞,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人如何能有這個經驗。這個跟人在看日出、看日落的那一條線,所產生的那種感性的能力其實非常的有關的。也就是說人好像在越過一條線的時候整(這)個世界都將變了!如此般的理想就是說那個時候的人,他有這樣的想法有這樣的理想的時候,這件事情如何透過作品呈現出來?這其實是海德格對藝術作品的一個想像。可是這個想像他沒辦法用更理性地詞去說清楚,他只能夠透過這個經驗。那再回到松志的這個作品,我覺得到最後他說「無法專心的煙」,我好奇的是這邊有抽菸的有多少人?都不抽菸喔?所以都很乾淨!我們的世界都變得好乾淨,不過我們把抽菸的人當作不乾淨這樣也不對。我的話題是想帶到有沒有人看過王家衛的電影?王家衛電影裡面常常拍抽菸的人,然後你們有沒有人記得王家衛怎麼樣拍煙?有沒有人記得?如果不記得你們回去可以找《花樣年華》、《墮落天使》或《重慶森林》,其實你們都會找到王家衛拍煙這件事情。其實你們在這個展場始終沒看到煙,都沒有看到煙?可是有看!我就在想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為什麼大家看到煙通常會覺得浪漫?或者說看到煙,也就是煙這件事除了你覺得是火災之外,會比較緊張,要不然通常我們看到煙其實人會有一種情緒上面的波動跟轉移。那也就是為什麼抽菸的人也很喜歡看到他自己吐出來的煙,好像那個煙可以改變他的節奏。但大家都不抽菸,可能感受不到!回家可以燒燒看會不會有感覺。可是王家衛的片子你會看到當他在拍煙的時候,那個菸其實它會突然很怪。他在拍梁朝偉抽菸,先拍梁朝偉的特寫,然後會有一絲煙往上跑出框外,緊接下來他的鏡頭會往上移或往上切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當他在拍梁朝偉的時候是一種時間的節奏,當他往上拍煙的時候完全變了,也就是我們會想起影片中梁朝偉所發生的過去。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效果,當我們在煙裡面的時候,為甚麼你會突然從一個現實空間跑到另外一個空間?這件事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為甚麼那麼喜歡去看河或海?為什麼我要提示這些經驗,因為這些經驗都很奇特,因為這些東西它就存在在我們現實世界裡面,可是這些東西的律動它會突然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想法。我在想其實在松志的這個展場裡當然是更為複雜,可是我覺得這個詩意是存在的。也就是這些關於律動的問題,關於我們如何透過著律動跑到另外一個狀態?這些東西在松志的創作裡面是非常重要,所以他的作品比如說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他沒有要告訴你太多關於任何議題,比如說他不會去談空氣汙染的問題,他也不去談Cosplay的問題,或者任何的政治議題,其實他都沒有要去談這些事情。可是在他的這些材料裡面,比如說我們剛踩進來的時候,我們踩在這些活性碳或踩在地毯上面,我們把活性碳壓的更碎或怎樣等等這些感受,就是說當你踩在地毯上跟你踩在一般的展場的地板上面的那種感覺經驗幾乎都不一樣了。剛剛在跟《藝術新聞》雜誌主編鄭乃銘聊的時候,其實我們突然都對一件事情異常的著迷,這個東西可以待會再看松志可以怎麼樣去談「詩」這件事情。我們突然感覺到「油」這件事情在這其中也是很重要的!你想想看喔,我們通常會覺得油,其實是一個連我自己都很不敢面對的事情,也就是說油要我自己面對的時候,好比在點滷肉飯、控肉飯的時候,其實會很期待那個油量,那個食物油亮的感覺!可是其實如果沒有食物擺在前面的時候,想到油這件事情就會想到自己,那是很殘酷的事情。所以往往都不大敢想油的這件事情。也就是說油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它到底在什麼樣的時刻會產生不至於讓你太快產生噁心的感覺?油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在很多時刻,我們在描述噁心的時候或這描述一些不好的感覺時候,其實會常用到油這件事情,油這個意象或油這個字。只是其實油這件事情如果把他拉回到這個展場裡,去感受或者去觀看松志所處理出來的「油感」,我覺得那裡面有一種感覺在生活裡面,有一種有趣的「油」!你回想看當你在看著你穿了很久的一雙布鞋,而你又很久沒有再回去穿它,然後當你有一天你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到底那雙鞋子剩下多少痕跡,也就是說在鞋子表面上的那個油亮其實是可以看出這雙鞋子的壽命或是說可以看到這雙鞋子的歷史。這其實是一個有趣的事情,那麼究竟什麼時候你所看到的那個油會變得漂亮?好比如果你剛請你喜歡的一個人到你的面前來喝個下午茶,喝完他回去了對不對,然後你在收杯子的時候,你發現杯子上有他的一個嘴唇印,不一定是口紅印,因為男的喝也會有留下那個非常薄的一層油,或者他手拿著杯子的所留下那一層薄的油痕。我會覺得其實在看松志的作品的時候,那般很薄層的這個感覺其實會變成是一個他帶給你記憶中很重要的痕跡。為甚麼我會特別去講這個,好像非常小的細節,這個待會可以看松志怎麼談。再來談到有關我所看到的這個空間,其實面對這個空間本身看完的第一次感覺,我看待這是一個被撕裂的空間,被撕碎的,那撕裂不是心理上的撕裂,並不是說這個空間是在談松志的創傷或是怎麼樣。而是這個空間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像是碎掉的!然後這個碎裂它有一個機會讓這個空間將不再是一個具體或具有某種形式的空間樣態。也是因為眾多這些碎掉東西的組成,我會突然的感覺這個空間它同時好像很豐富!因為他有很多很細很碎的東西,但它同時,讓你不曉的焦點在哪裡?重點在哪裡?我覺得這是這次松志他在做這個空間裡頭給我的另外一個驚喜。這是我察覺他在空間處理的特質,因此我特別將它先提出來。除這點之外還有另外一點跟空間有關的提問,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越來越多年輕藝術家,其實都對於處理空間越來越感興趣。這方面可以當未來有機會可以再聊,可是我們就先回到有關處理空間的個部分看看松志有沒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陳松志:其實剛剛建宏老師有提到一個時間性的問題,還有提到所謂的地景這件事情,我想當我們踩踏在這個空間一進來時你會連結到地表或是地貌,其實我在做這個展覽的過程當中,讓我去思考到一件事情,某種表面上所看起來的「寧靜」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假象,就像人的思考其實是它隱藏在你的腦內,你也許看起來是一個很靜態的狀況,但事實上你的身體、你的意識其實是一直不斷的在動的。那這個其實讓我回想到就是說我聽過一個諺語:「人將不會踏在同一條河流之中」,因為那個河底的時間是一直不斷的在流動的。那當我們再探討到時間這個趣味點,其實時間是被人所定義出來,包括時區,有關時區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假的界線,也許透過人為的經緯度,來劃做所謂的時區,我認為區分這個界線如同是在找形(界線)的過程?那究竟找什麼是形這件事情?就變的相當有趣了。剛剛建宏老師提到一個所謂撕碎的這個世界,其實我覺得尋找的過程,就像我們如同在進行拼圖,或者是你把一張原本被撕碎掉的形之後,你怎麼去收拾這個殘局去找回它原本的形態。這個動機其實是源自於時間、空間之後,作為一個創作者他會因應生活裡的事件、去回應處理這些現實狀態的總總,在這些產生的擾動影響裡,創作者他在進行塑型、找形的這動作。我常常運用到很多所謂不穩定性的材質,我覺得這個不穩定性我一方面想要凝固它,但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它們永遠有一個物理的原則,它在抵抗這個非物理的環境。我覺得在這個尋找的過程它反而是一個界於起始跟最後看到結果之間,我倒覺得那個過程反而是一個「經過本身」是最有趣的狀態。剛剛建宏老師有提到很多王家衛的電影,包括抽菸這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看到人家抽菸或是你自己抽菸的時候,你會發現為什麼人要抽菸?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你希望在這個持續的生活進行當中,它留住某一個短暫的片刻,你必須放下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來專注一件事情,我覺得那是一個假象靜止的時間,時間並沒有因此而停住。我們將重心建構在一根菸的消逝,另外一個煙的揮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我覺得這裡頭關乎作品中剛提到那些所謂流動性的這些、流變性的這些物質,它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要讓這些消逝跟介入的東西,它們同時並存在這個狀態,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相對的。那再回到建宏老師提到「油」的部分,我覺得人的身體需要有油,但也同時需要有水,可是油跟水本身其實是相斥的,但在我們的身體機能油和水其實是需要達成某一種平衡的關係,它才能共存,否則其實它就失衡。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放到我們思考到生命體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滿關鍵的一個成分在這裡頭。首先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有關於這個「變」的這件事情,其實我們身體不斷的在變,你每天吃的油脂、你喝的水,它就是一個不定型,我們永遠覺得我們的鞋子固定是穿幾號、身體是穿什麼尺碼,可是其實你的身體是不斷的在收縮跟放大的,那是一個很彈性的變化。我的創作其實是某種程度上是在顯現追求那個彈性的本身,而不是在尋找那個最放的、跟最收縮極致的狀態。
黃建宏:我在想把機會給來的現場朋友,有沒有人要提問的?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你們剛剛都有在「無法專心的煙」現場感覺嗎?
陳松志: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我想補充一個我的觀察,其實剛剛大約兩點鐘的時候作品現場陸陸續續有一些人,包括剛剛這些來參觀的朋友們,其實在現場我看到一個滿有趣的景象,我覺得那個現場很多人在其中大致看起來很像是「失魂」。原因在於在這個空間裡其實你也不知道你要看哪裡?然後你又沒辦法專心跟你的對象聊天!因為你其實知道腳下這個地毯表面充滿了不穩定性以及作品本身它滿脆弱的。或者是你也不希望那個粒子掉到你的鞋子裡頭或弄髒你自己的鞋,還有一直不斷的聲響,它不斷地擾亂你的身體的各種感覺。所以其實變成大家在裡頭走動的時候,其實非常的不自在,這件作品同時引出了你最多的感覺然後感覺盡出,最後我形容有點像是喪屍,或者是那種我們講失魂落魄的樣子。這是我觀察到的一個現場狀態覺得還滿有趣的。
黃建宏:有沒有人要講一下?我想你們現在不會只是觀眾,你們已經進到這個畫廊主人已經在這裡奮鬥十年,你們就坐在她們奮鬥的地方,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陳松志:我想這個今天這個活動,就是我們被濃縮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擠下這麼多具有油脂、水分的人,這個所謂生命體,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看到就在藝術其實給藝術家最大的空間,它願意把所有最大的空間提供給藝術家,然後我們今天大家集中在這麼一個角落裡頭,為了是能提供藝術家最完整的創作空間,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尺度了。
黃建宏:大家沒有想要講什麼嗎?如果沒有,你們要繼續聽我講事情嗎?我講事情會很像上課喔!真得要繼續講吼?我們來就是我剛剛其實有預設丟出一個問題,大概也是我對所有藝術家的展覽,剛剛其實有提到一件事情可以再補充一下,剛才有談到分子這件事情,也就是對於材料的選取,開始去選一些吸收性的、有所謂的專一性的那種材料,一些特殊、特性的材料,一直到松志對於「詩的意象」裡的堅持,也就是說從那種我們對分子世界想像那種流動性,一直到那種詩的意象的那種想像,其實它的層次跨越的非常大。如果這回到我作為一個觀者本身,我對藝術家的展覽其實都有一種期望,藝術家是一個個體,基本上作為一個個體,那他在進行表達的時候,這個時候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翻轉出一個我們開始對比較不是那麼只是自己問題的問題去進行思考或想像。這件事情會讓我想到一件事,因為昨天是北藝大這屆的畢業展,這屆畢業展發現有好多年輕人都做跟空間有關的創作,當然大部分跟空間有關的創作其實他們基本上最大的特質都專注在劇場式的空間,也就是讓空間具有某種敘事的感覺。他們都是大學部,當然有很多地方都還不夠成熟跟精準,可是我在想現在的人到底為什麼對空間有一種特別的期待,而不是非常專注的在做作品?其實有一個很殘酷的事情是什麼?也就是說在普遍學院裡都有的現象,有一些比較有進步精神的老師,有時候就會告訴學生說你為什麼要那麼作品化?也就是在學院裡的創作就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那麼作品化的呈現嗎?你為何要把你自己那麼封閉在一個物件上面嗎?或者一幅畫面上?通常這樣的事情對於年輕的藝術家來講,就是還在學習的學生藝術家來講,他馬上會產生一種迷惘,其實松志也是老師,也可以參與在這裡面談。這個迷惘就是要如何做出不像作品的作品?我不做出那個物件,那我要做什麼?通常同學其實如果先擺脫做物件或做物品這件事情,是一個制式化或體制所想像的事情的話,那在創作中越出這件事情我到底可以幹嘛?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人都會先往空間走,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空間究竟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希望?為什麼我們從體制的一個規範,就是我們就是要做作品的這件事情脫離的時候,大家會先去想空間?我會覺得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人,如同我一剛開始講的,即使這個地方現在是你沒有去過的,那個地方對你來講可能都是已知的,因為我們今天有太多的訊息告訴你什麼空間就是什麼用途?什麼空間你可以做什麼事?甚至連白盒子之外到底我們可以幹嘛都經非常清楚,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空間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或者相對相反過來,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年輕學生藝術家他們對空間有一種非常大的嚮往,我會覺得其實這跟姚瑞中他們年輕的時候,當他還是北藝大學生的時候,然後他們去佔領一個地方然後叫做「非常廟」那動機是非常不一樣的,那個非常不一樣的狀態是說,當時他們這些年輕人佔領一個空間,那些空間是沒有人管的!可是其實今天為什麼年輕人對空間有一種很像一種渴望,可是又表示這可望非常難實現,我想就是現在即使是廢棄的地方,看起來像是廢墟的地方都有產權,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對於空間的想像其實會因為所有的空間在城市裡面都越來越被產權化,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空地沒有人要,然後隨便你去做任何事,這種機會已經非常非常少!更何況來念藝術做當代藝術,大部分都在城市裡面,其實這件事情就更難被發生。因此我會覺得就是在這個狀況底下,如何帶出如何有能力把一個空間做出我要的感覺!把一個空間做成什麼感覺?這裡面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慾望,所以我覺的應該是在一個空間取得一個越難的地方,或越嚴苛的地方,其實藝術家會越被逼往這個方向去思考。也就是說我如何創造出因為這很像煙霧一樣,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到一個地方展覽,其實除非你跟這個屋主或這個所有權的人有建構某種常態的關係,你才有可能永遠留存在這個空間,要不然其實這些空間都很像煙霧一樣,藝術家在面對一個檔期,到底可以留下什麼?除了交易紀錄之外,就是說你待會在一個空間可以留下什麼?這其實會變成一個藝術家需要挑戰的事情!雖然大部分的藝術家還是選擇用作品,因為其實這個最簡單,就很像當你像想不出你要買什麼東西給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時候,通常就是買一個小東西,因為小東西最簡單。所以其實到底怎麼樣去讓一個空間有不同的感覺,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會成為今天年輕人的一個慾望,我不曉得松志你也當老師也是一位藝術家你怎麼來思考?
陳松志:其實常有人會問我到底我的創作是什麼類型?什麼屬性?我其實比較會去強調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是在處裡複合媒體在空間現場裡頭的現地呈現。基本上我們會簡稱為現地裝置或空間裝置。其實我要選用什麼材料它都是多重選擇,所以基本上去取決於先有空間才知道要放什麼素材進去,所以這些空間本身它的架構它的基礎可能都跑在我的原先我的發現、我的收集以及設想之前。也許你收集了原本生活裡頭你的感性它根本放不進那個空間,因為這些空間本身它太強大了,因為我覺得任何空間,白盒子有白盒子空間的強大,黑盒子或者是一個廢墟在透過藝術行為介入它都需要面臨不同挑戰的層面。剛剛建宏老師其實提到的一點人嚮往廢墟,因為在那個廢墟當中,你往往可以看到從廢墟裡頭長出來的一株小草,或者是你還存在在這裡,它還有某一種生命在這個看似快要無機的狀況下,它產生出來的一個力道。反過來講,我覺得其實在一個廢墟空間來創作,我認為那是很容易借力使力,因為廢墟本身就很豐富!它本身就很多歷史的痕跡層次在那裡頭。我反倒覺得對我來講在白盒子做空間它相對是難的,因為白盒子很明顯就是垂直水平的線軸不斷地轉折在這裡頭,那如何把那條線拿掉?我如何在這裡頭製造出一個可能往廢墟走的意象?也許它是一種心理層次的廢墟,因為我不可能製造出一個真的廢墟,或是趨近於真正廢墟的一個空間,所以為什麼我在處裡「就在」這麼多次經驗裡頭,我覺得越對它越瞭解才知道它的難處,那因為這個難處其實我希望用另外一個方式去面對它!你也可以在這次展覽裡頭看到幾個黑色的布幔,這個畫廊看起來很完整,天花板挑高也夠高,可是它還是有一個它原本畫廊空間裡頭的痕跡跟造型,再加上它必需要符合某種機能性,比如說這裡要有辦公室、這裡要有通道,老實講對我來講如果我要一個純白的空間就只要讓大家看見作品,其實這些辦公室的開口、廊道所產生出來的洞孔跟光線,對我來講就是干擾!我如何把這個干擾涵蓋進去?像茶水間它需要有一個排風口,因為要有冷氣傳送,那我索性把排風口變成一個聲道,讓它感覺從茶水間裡你有股另一個很日常生活裡頭播放著的持續音樂,它是一個很生活的情狀串流。然後在很多縫隙的空間裡頭我夾了一些廣播的現場,那些內容其實不是我主導,它是一個調頻,它其實一直持續在進行的,它是一直在變的現場空間延伸,那有什麼是不變?你看到的那幾個黑色的布幔它其實根據這個空間入口尺寸一比一,量尺的尺規,變成一個遮蔽的通道,它暗示著這裡好像有另外一個空間,它變成另外一個造型,它形成了一個對照的關係。因此你說這幾個黑色尺寸它離開這個空間它可能就失去意義,因為它是之於這個空間它們有一個相對的一個角色對位關係在這裡頭。我總歸來講,這裡頭有太多太多的線索,如果我們用詩詞的方式來建構或表達這件事情,如何讀懂一首詩其實是滿深的學問。雖然詩的結構並不長,但詩基本上在很有限的文字裡頭,必須創造出最多意境,創造出最多豐富層次的語境,或者是語意。那裡頭其實有各方的詮釋,懂不懂不重要,如何想要讀懂?或是在讀的過程,就是一個滿重要的體驗。所以對於這個「無法專心的煙」它其實涵蓋了的就是這麼一段找尋的過程。
黃建宏:那個時間就是快差不多,我在想大家有沒有一定要追問的問題或者說要問的問題,可以趁這個機會來問藝術家,我在想就是說台灣的藝術家應該有快二十年年輕藝術家其實都在思考到底要怎麼抓住稍縱即逝,或者說瞬間,也就是說不會留太久的東西。那種感覺到底要怎樣被掌握住?然後雖然它在非常短的瞬間發生的事情,它在這麼小的瞬間又一直在變,其實有非常多藝術家都在想這件事,可是我們會發現雖然大家在唸書的時候有很多藝術家在想這件事,可是你會發現當很多藝術家開始進入藝術圈開始進行專業的創作的時候,越來越少藝術家還那麼專注來面對這個問題,因為這個東西它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大部分藝術家還是會選擇建立風格,所以這裡面並不是在講風格是好或不好,而是要讓人家知道說你這風格是像設計一個Logo那麼快就成立了。還是你這風格其實讓大家講不清楚那裡面到底有什麼,這其實也可以變成另一種風格的發展。松志的創作風格究竟是哪一個?我想這就留給大家可以再去想一下,可以再跟松志繼續交流的一個問題,我想大家都比較想要跟他私聊,私聊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事情,那我們今天就先謝謝就在藝術給我們這個難得的機會,然後再謝謝松志。謝謝大家今天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