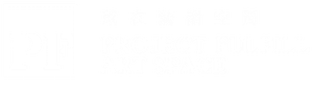Obliteration
An Exhibition of Ou Jing-Yun, Peng Yu-Tzu, and Chen Jun-Yu
《爛石與枯海》歐靜雲、彭禹慈、陳俊宇三人展
藝術家 Q & A 與策展人陳松志
歐靜雲
陳松志:對你而言,你的繪畫在這個時代中的特殊意義是什麼?
歐靜雲: 繪畫從機械複製的時代就開始被宣判死亡,到現在混合實境、超媒體逐漸成為我們生活觀看的方法,繪畫一直死死生生,在這個時代畫家擁有的多半都是繪畫的屍塊或是回返的亡魂。時代過於的巨大,大到無法定義,繪畫最特殊的意義就是他仍然用一種幽靈的方式存在著,仍藉著身體的勞動壓榨出我們對可見之上創造力的某種分享。
陳松志: 有哪一個藝術家(或作品)是你創作研究中的關鍵影響?
歐靜雲: Jeff Wall的《Dead Troops Talk》我認為這件作品很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作者如何利用視覺形式拼貼、拆解或拼裝我們曾未企及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感知經驗,我認為這也是具象繪畫、具象形式中不可逃避的問題,我們如何在畫、拍、塑、書寫等等的“製造”與“觀看”中創造或再創造圖像的意義。
陳松志: 如果面對一個視盲者你會怎麼跟他導讀你的作品?
歐靜雲: 這個問題很困難,我曾經想過如果有一天我主動或被動放棄視力之後我還能不能從事繪畫的行為,那可能是記憶的召喚或是一種感受類比的東西之外的⋯⋯我會試著朗讀我這張畫從構思(未明)到執行(將明)的過程。
陳松志:在這次展出的系列作品中,相較過往創作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
歐靜雲:風景畫在古典某種程度有一種紀實與收集的慾望,我在這次展出的若干件作品中特別談的各種景:是存與不存間的各種落差帶來的空缺與失落。
陳松志:對你而言,你的繪畫在這個時代中的特殊意義是什麼?
歐靜雲: 繪畫從機械複製的時代就開始被宣判死亡,到現在混合實境、超媒體逐漸成為我們生活觀看的方法,繪畫一直死死生生,在這個時代畫家擁有的多半都是繪畫的屍塊或是回返的亡魂。時代過於的巨大,大到無法定義,繪畫最特殊的意義就是他仍然用一種幽靈的方式存在著,仍藉著身體的勞動壓榨出我們對可見之上創造力的某種分享。
陳松志: 有哪一個藝術家(或作品)是你創作研究中的關鍵影響?
歐靜雲: Jeff Wall的《Dead Troops Talk》我認為這件作品很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作者如何利用視覺形式拼貼、拆解或拼裝我們曾未企及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感知經驗,我認為這也是具象繪畫、具象形式中不可逃避的問題,我們如何在畫、拍、塑、書寫等等的“製造”與“觀看”中創造或再創造圖像的意義。
陳松志: 如果面對一個視盲者你會怎麼跟他導讀你的作品?
歐靜雲: 這個問題很困難,我曾經想過如果有一天我主動或被動放棄視力之後我還能不能從事繪畫的行為,那可能是記憶的召喚或是一種感受類比的東西之外的⋯⋯我會試著朗讀我這張畫從構思(未明)到執行(將明)的過程。
陳松志:在這次展出的系列作品中,相較過往創作有什麼特別不同之處?
歐靜雲:風景畫在古典某種程度有一種紀實與收集的慾望,我在這次展出的若干件作品中特別談的各種景:是存與不存間的各種落差帶來的空缺與失落。
彭禹慈
陳松志:抽象繪畫對妳而言,具有什麼吸引力?
彭禹慈:“精神性”是抽象畫跟裝飾性的分界,對於我來說這是抽象繪畫的吸引處,而繪畫作為二度空間,精神性跨越的第一步,他不需要跟這個世界一樣,他擁有獨立性,且繪畫是精神性的反芻,表面即深度,而這深度是跟精神性緊密的。而我最想努力做到的是關於內在真實,脫離畫作表面上所能看到的,重視思維的原始狀態,透過繪畫來達到某種聯想形式層次更高的真實。
陳松志:在妳的繪畫中特別著重,以筆觸來表現『碎形』(或是不完整的輪廓),背後有沒有什麼隱喻?
彭禹慈:『碎形』以一種圖像被延遲,作用在我的認知裡,我們觀看經驗也一直被延遲著,而時間被塞入了,產生圖像的生命,而圖像的生命他們會不停的變化和生長,而會留下痕跡——我的『碎形』的歷程,即使有些記憶編織的影像總是充滿了能夠驅動和擾亂身體的能量,而某些記憶已經掉了,但仍在作用著我們的身體,而當我們想記憶某些,慾望會攪動,圖像會脫離掌控,圖像是漫身式的擴散。
陳松志:如果妳的創作可以搭配一段音樂,你會希望是什麼?為什麼?
彭禹慈:從創作關注的脈絡中,呼應所關注的思維以及留白、負空間,我的第一個想法是:John Cage的Silence,悅音被沈默給取代了,開始聽到噪音、環境音等等,所有的聲音都是平等的,很重要的是聆聽這件事情,而這段時間裡的所有,這些不可計算的變化、和意識上轉換等等,而回歸到繪畫,任何建立於畫布上的色彩、顏料等等都是存在的,包含那些不被敷上顏料的空白,它也同等重要。
陳松志:新作之中有更多對於空白(負的空間)的表現,在這系列之中,你希望帶給觀眾什麼視覺經驗?
彭禹慈:關於留白以及負空間,像是將創作者心中的現實凸顯出來,而這現實不只是現實,它也可能是往精神去對話的,創作者本身所思考的狀態,而畫面的視覺都是相互牽引的,而對於我而言,白色是一項能切實並深刻揭露繪畫真相的創作方式,而回歸到繪畫,白色像是精神性的敏感區域,視覺知識的組織化交付給觀者。
陳松志:抽象繪畫對妳而言,具有什麼吸引力?
彭禹慈:“精神性”是抽象畫跟裝飾性的分界,對於我來說這是抽象繪畫的吸引處,而繪畫作為二度空間,精神性跨越的第一步,他不需要跟這個世界一樣,他擁有獨立性,且繪畫是精神性的反芻,表面即深度,而這深度是跟精神性緊密的。而我最想努力做到的是關於內在真實,脫離畫作表面上所能看到的,重視思維的原始狀態,透過繪畫來達到某種聯想形式層次更高的真實。
陳松志:在妳的繪畫中特別著重,以筆觸來表現『碎形』(或是不完整的輪廓),背後有沒有什麼隱喻?
彭禹慈:『碎形』以一種圖像被延遲,作用在我的認知裡,我們觀看經驗也一直被延遲著,而時間被塞入了,產生圖像的生命,而圖像的生命他們會不停的變化和生長,而會留下痕跡——我的『碎形』的歷程,即使有些記憶編織的影像總是充滿了能夠驅動和擾亂身體的能量,而某些記憶已經掉了,但仍在作用著我們的身體,而當我們想記憶某些,慾望會攪動,圖像會脫離掌控,圖像是漫身式的擴散。
陳松志:如果妳的創作可以搭配一段音樂,你會希望是什麼?為什麼?
彭禹慈:從創作關注的脈絡中,呼應所關注的思維以及留白、負空間,我的第一個想法是:John Cage的Silence,悅音被沈默給取代了,開始聽到噪音、環境音等等,所有的聲音都是平等的,很重要的是聆聽這件事情,而這段時間裡的所有,這些不可計算的變化、和意識上轉換等等,而回歸到繪畫,任何建立於畫布上的色彩、顏料等等都是存在的,包含那些不被敷上顏料的空白,它也同等重要。
陳松志:新作之中有更多對於空白(負的空間)的表現,在這系列之中,你希望帶給觀眾什麼視覺經驗?
彭禹慈:關於留白以及負空間,像是將創作者心中的現實凸顯出來,而這現實不只是現實,它也可能是往精神去對話的,創作者本身所思考的狀態,而畫面的視覺都是相互牽引的,而對於我而言,白色是一項能切實並深刻揭露繪畫真相的創作方式,而回歸到繪畫,白色像是精神性的敏感區域,視覺知識的組織化交付給觀者。
陳俊宇
陳松志:是在什麼契機下誘發了你開始將身體作為個人創作的表達?
陳俊宇: 真的開始行為創作是大三那年。其實一直都有想過用身體創作,所以在一次作品難產的情況下,我試著想像我還有什麼材料是可以使用的?於是誤打誤撞就做了第一件行為創作。一直以來我都有強烈的表演慾望,或許就在那次的展覽壓力下全部被釋放出來了。
陳松志: 行為創作對你而言最需要克服的恐懼是什麼?
陳俊宇: 對我來說行為創作並沒有要克服什麼恐懼,如果真的要說的話,我更需要的是相信,相信自己能夠站在那把展演現場完成。
陳松志: 你認為是你需要觀眾?還是觀眾需要你的身體?
陳俊宇: 我認為是我需要觀眾,在我的創作中,我提出來的或是行為呈現的,更多是提出一種更多元的想像。試圖透過特種的視覺經驗提供一個共同理解與討論的平台。
陳松志:在這次發表的新作,你希望帶給帶給觀眾什麼新思考?
陳俊宇: 在這次的作品《_USED TO》中,「一直把自己留在這裡」作為貫穿作品的一句話。其實在我的創作中,我經常有大量重複的動作,我其實是在談一種生活的當機。透過當機的卡住、LAG 作為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狀態。透過一直不斷描繪、雕刻自己的型態就像是不停地一遍又一遍的看到自己存在的軌跡。有點像是透過一種儀式性的方式去看到自己曾經在哪裡?是如何存在又如何曾經存在?
陳松志:是在什麼契機下誘發了你開始將身體作為個人創作的表達?
陳俊宇: 真的開始行為創作是大三那年。其實一直都有想過用身體創作,所以在一次作品難產的情況下,我試著想像我還有什麼材料是可以使用的?於是誤打誤撞就做了第一件行為創作。一直以來我都有強烈的表演慾望,或許就在那次的展覽壓力下全部被釋放出來了。
陳松志: 行為創作對你而言最需要克服的恐懼是什麼?
陳俊宇: 對我來說行為創作並沒有要克服什麼恐懼,如果真的要說的話,我更需要的是相信,相信自己能夠站在那把展演現場完成。
陳松志: 你認為是你需要觀眾?還是觀眾需要你的身體?
陳俊宇: 我認為是我需要觀眾,在我的創作中,我提出來的或是行為呈現的,更多是提出一種更多元的想像。試圖透過特種的視覺經驗提供一個共同理解與討論的平台。
陳松志:在這次發表的新作,你希望帶給帶給觀眾什麼新思考?
陳俊宇: 在這次的作品《_USED TO》中,「一直把自己留在這裡」作為貫穿作品的一句話。其實在我的創作中,我經常有大量重複的動作,我其實是在談一種生活的當機。透過當機的卡住、LAG 作為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狀態。透過一直不斷描繪、雕刻自己的型態就像是不停地一遍又一遍的看到自己存在的軌跡。有點像是透過一種儀式性的方式去看到自己曾經在哪裡?是如何存在又如何曾經存在?